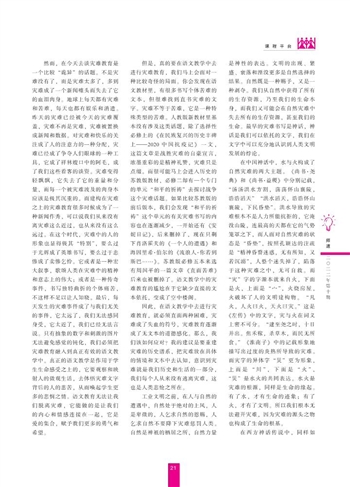然而,在今天去谈灾难教育是一个比较“诡异”的话题。不是灾难没有了,而是灾难太多了,多到灾难成了一个新闻噱头而失去了它的血泪肉身。地球上每天都有灾难和苦难,每天也都有娱乐和消遣。昨天的灾难已经被今天的灾难覆盖,灾难不再是灾难,灾难被置换成新闻和数据。对灾难和快乐的关注成了人的注意力的一种分配,灾难已经成了争夺人们眼球的一种工具,它成了祥林嫂口中的阿毛,成了我们这些看客的谈资。灾难变得轻飘飘,它失去了它的重量和分量,而每一个被灾难波及的肉身本应该是极其沉重的。而建构在灾难之上的灾难教育很多时候成为了一种新闻作秀,可以说我们从来没有离灾难这么近过,也从来没有这么远过。在这个时代,灾难中的人的形象也显得极其“特别”,要么过于光辉成了英雄书写,要么过于悲惨成了卖惨乞怜。它或者是一种宏大叙事,歌颂人类在灾难中的精神和意志上的伟大;或者是一种传奇事件,书写独特曲折的个体痛苦,不这样不足以让人知晓。最后,每天发生的灾难事件成了与我们无关的事件,它太远了,我们无法感同身受,它太近了,我们已经无法言说。只有抽象的数字和刺激的图片无法避免感觉的钝化,我们必须把灾难教育融入到真正有效的语文教学中。真正的语文教学是作用于学生生命感受之上的,它要观察和映射人的微观生活,去体悟灾难文字背后的人的悲苦,从而唤起学生更多的悲悯之情。语文教育无法让我们脱离灾难,它能做的是让我们的内心和情感连接在一起,它是爱的集合,赋予我们更多的勇气和希望。
但是,真的要在语文教学中去进行灾难教育,我们马上会面对一种比较奇怪的局面。你会发现在语文教材里,有很多书写个体苦难的文本,但很难找到直书灾难的文字。灾难不等于苦难,它是一种特殊类型的苦难。人教版新教材里基本没有涉及这类话题,除了选择性必修上的《在民族复兴的历史丰碑上——2020中国抗疫记》一文,这篇文章是战胜灾难的自豪宣言,浓墨重彩的是精神礼赞,灾难只是点缀。而很可能马上会进入历史的苏教版教材,必修二却有一个专门的单元“和平的祈祷”去探讨战争这个灾难话题。如果比较苏教版的前后版本,我们会发现“和平的祈祷”这个单元的有关灾难书写的内容也在逐渐减少,一开始还有《安妮日记》,后来删掉了,现在只剩下肖洛霍夫的《一个人的遭遇》和海因里希·伯尔的《流浪人·你若到斯巴……》。苏教版必修五本来选有周国平的一篇文章《直面苦难》后来也被删掉了。语文教学中的灾难教育的尴尬在于它缺少直接的文本依托,变成了空中楼阁。
因此,在语文教学中去进行灾难教育,就必须直面两种困难,灾难成了失血的符号,灾难教育逐渐成了无文本的道德感化。那么,我们该如何应对?我的建议是要重建灾难的历史谱系,把灾难放在具体的情境和文本中去认知,意识到灾难就是我们历史和生活的一部分,我们每个人从来没有逃离灾难,这也是人类悲怆之所在。
工业文明之前,在人与自然的遭遇中,自然处于绝对的上风,人是卑微的,人乞求自然的恩赐,人乞求自然不要降下灾难惩罚人类。自然是神祇的栖居之所,自然力量是神性的表达。文明的出现、繁盛、衰落和湮没更多是自然选择的结果。自然既是一种赐予,又是一种剥夺。我们从自然中获得了所有的生存资源,乃至我们的生命本身,而我们又可能会在自然灾难中失去所有的生存资源,甚至我们的生命。最早的灾难书写是神话,神话是我们可以依托的文字,我们在文字中可以充分地认识到人类文明发展的悖论。
在中国神话中,水与火构成了自然灾难的两大主题。《尚书·尧典》和《尚书·益稷》中分别记载,“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昏垫”。洪水导致的灾难根本不是人力所能抗拒的,它淹没山陵,连最高的天都在它的气势笼罩之下,而人面对自然灾难的状态是“昏垫”,按照孔颖达的注疏是“精神昏瞀迷惑,无有所知,又若沉溺”,人整个迷失掉了,陷落于这种灾难之中,无可自救。而“灾”字的字源本就来自火,下面是火,上面是“宀”,火烧房屋,火破坏了人的文明建构物。“凡火,人火曰火,天火曰灾。”这是《左传》中的文字,灾与火在词义上密不可分。“逮至尧之时,十日并出。焦禾稼,杀草木,而民无所食。”《淮南子》中的记载形象地描写出过度的炎热所导致的灾难。而灾字的异体字“災”更为形象,上面是“川”,下面是“火”,“災”是水火的共同表达。水火是灾难的根源,同样是生命的缘起。有了水,才有生命的迹象;有了火,才有了文明。所以我们根本无法避开灾难,因为灾难的源头之物也构成了生命的根基。
在西方神话传说中,同样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