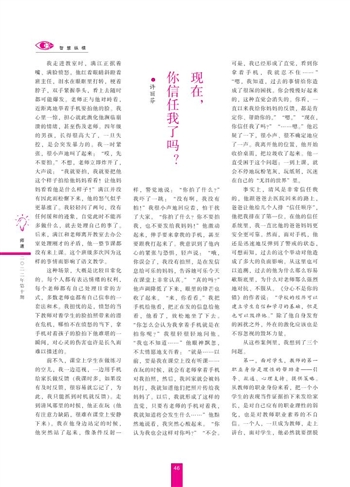■ 许丽芬
我走进教室时,满江正抿着嘴、满脸愤怒。他红着眼睛斜瞪着班主任,泪水在眼眶里打转,梗着脖子,双手紧握拳头,看上去随时都可能爆发。老师正与他对峙着,近距离地举着手机要拍他的脸。我心里一惊,担心就此激化他濒临崩溃的情绪,甚至伤及老师。四年级的男孩,长得很高大了,一旦失控,是会突发暴力的。我一时紧张,很小声地叫了起来:“哎,先不要拍。”不想,老师立即炸开了,大声说:“我就要拍,我就要把他这个样子拍给他妈妈看看!让他妈妈看看他是什么样子!”满江并没有因此而松懈下来,他的怒气似乎更暴涨了。我轻轻问了两句,没有任何缓和的迹象,自觉此时不能再多做什么,就去处理自己的事了。后来,满江和老师离开教室去办公室处理刚才的矛盾,他一整节课都没有来上课。这个班级多次因为这样的事情而影响了语文教学。
这种场景,大概是比较日常化的。每个人都有表达情绪的权利,每个老师都有自己处理日常的方式,多数老师也都有自己信奉的一套法和术。我担忧的是,愤怒的当下教师对着学生的脸拍照带来的潜在危机,哪怕不在愤怒的当下,拿手机对着孩子的脸拍下他难堪的一瞬间,对心灵的伤害也许是长久而难以描述的。
前不久,课堂上学生在做练习的空儿,我一边巡视,一边用手机给家长做反馈(我课时多,如果没有及时反馈,很容易就忘记了,为此,我只能抓到时机就反馈)。走到清风那里的时候,他正在玩(他有注意力缺陷,很难在课堂上安静下来)。我在他身边站定的时候,他突然站了起来,像条件反射一样,警觉地说:“你拍了什么?”我吓了一跳:“没有啊,我没有拍!”我很小声地回应着,怕干扰了大家。“你拍了什么?你不要拍我,也不要发给我妈妈!”他激动起来,伸手要来拿我的手机,甚至要跟我打起来了。我意识到了他内心的紧张与恐惧,轻声说:“哦,你误会了,我没有拍照,是在发信息给可乐的妈妈,告诉她可乐今天在课堂上非常认真。”“真的吗?”他声调降低了下来,眼里的锋芒也收了起来。“来,你看看。”我把手机给他看,把正在发的信息给他看,他看了,放松地坐了下去。“你怎么会认为我拿着手机就是在拍你呢?”我很轻很轻地问他。“我也不知道……”他眼神飘忽,不太情愿地支吾着:“就是……以前,要是我在课堂上没有听课……在玩的时候,就会有老师拿着手机对我拍照,然后,我回家就会被妈妈打,我就知道他们把照片传给我妈妈了。以后,我就形成了这样的直觉,只要有老师的手机对着我,我就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他黯然地说着,我突然心酸起来。“你认为我也会这样对你吗?”“不会。可是,我已经形成了直觉,看到你拿着手机,我就忍不住……”“嗯,我知道,过去的事情给你造成了很深的困扰。你会慢慢好起来的,这种直觉会消失的。你看,一直以来我给你妈妈的反馈,都是肯定你、帮助你的。”“嗯。”“现在,你信任我了吗?”“……嗯。”他迟疑了一下,很小声、很不确定地应了一声。我离开他的位置,他开始收拾桌面,把垃圾收了起来。他一直受困于这个问题:一到上课,就会不停地玩粉笔灰,玩纸屑,沉迷在自己的“无目的世界”里。
事实上,清风是非常信任我的,他跟爸爸去医院回来的路上,爸爸让他给几个人排“信任顺序”,他把我排在了第一位。在他的信任系统里,我一直比他的爸爸妈妈更安全更可靠。然而,面对手机,他还是迅速地反弹到了警戒的状态,可想而知,过去的这个举动对他造成了多大的负面影响。从这里也可以追溯,过去的他为什么那么容易歇斯底里,为什么对老师那么强烈地对抗、不服从。《分心不是你的错》的作者说:“学校的经历可以建立学生自信和学习的基础,但是也可以毁掉他。”除了他自身发育的困扰之外,外在的激化应该也是不容忽视的毁坏力量。
从这些案例里,我想到了三个问题。
第一,面对学生,教师的第一职业身份是理性的帮助者——引导、疏通、心理支持、提供策略。从教师的职业身份来看,把一个小学生的表现当作证据拍下来发给家长,是对自己应有的职业理性的弱化,也是对教师职业素养的不自信。一个人,一旦成为教师,走上讲台,面对学生,他必然就要摆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