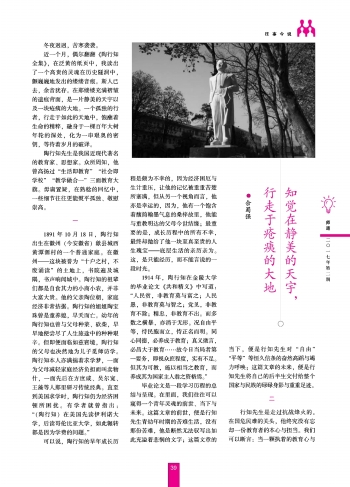冬夜迥迥,苦寒袭袭。
近一个月,偶尔翻翻《陶行知全集》,在泛黄的纸页中,我读出了一个高贵的灵魂在历史隧洞中,颤巍巍地发出的缕缕音痕。斯人已去,余音犹存。在那缕缕充满褶皱的遗痕背面,是一片静美的天宇以及一块疮痍的大地。一个孤独的行者,行走于如此的天地中,饱蘸着生命的精粹,融身于一棵百年大树年轮的深处,化为一串艰奥的密钥,等待着岁月的破译。
陶行知先生是我国近现代著名的教育家、思想家。众所周知,他曾高扬过“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三面教育大旗。毋庸置疑,在熟稔的回忆中,一些细节往往更能熨平孤独、敬慰崇高。
一
1891年10月18日,陶行知出生在徽州(今安徽省)歙县城西黄潭源村的一个普通家庭。在徽州——这块被誉为“十户之村,不废诵读”的土地上,书院遍及城隅,书声响闻城中。陶行知的祖辈们都是自食其力的小商小农,并非大富大贵。他的父亲陶位朝,家庭经济非常拮据。陶行知的姐姐陶宝珠曾是童养媳,早夭而亡。幼年的陶行知也曾与父母种菜、砍柴,早早地便尝尽了人生旅途中的种种艰辛。但即便面临如兹窘境,陶行知的父母也决然地为儿子觅师访学。陶行知本人亦满揣着求学梦,一面为父母减轻家庭经济负担而叫卖物什,一面先后在方庶咸、吴尔宽、王藻等人那里研习传统经典。直至到美国求学时,陶行知仍为经济困顿所困扰。有学者就曾指出:“(陶行知)在美国先读伊利诺大学,后读哥伦比亚大学,如此辗转都是因为学费的问题。”
可以说,陶行知的早年成长历程是颇为不幸的,因为经济困厄与生计重压,让他的记忆被重重苦楚所塞满,但从另一个视角而言,他亦是幸运的,因为,他有一个饱含着馥韵翰墨气息的桑梓故里,他能与重教明达的父母今世结缘;最重要的是,成长历程中的所有不幸,最终却抛给了他一块至真至贵的人生瑰宝——底层生活的亲历亲为。这,是只能经历,而不能言说的一段时光。
1914年,陶行知在金陵大学的毕业论文《共和精义》中写道:“人民贫,非教育莫与富之;人民愚,非教育莫与智之;党见,非教育不除;精忠,非教育不出。而多数之横暴,亦消于无形。况自由平等,恃民胞而立,恃正名而明。同心同德,必养成于教育;真义微言,必昌大于教育……故今日当局者第一要务,即视众庶程度,实有不足。但其为可教,施以相当之教育,而养成其为国家主人翁之资格焉。”
毕业论文是一段学习历程的总结与呈现。在里面,我们往往可以窥得一个青年灵魂的前世、当下与未来。这篇文章的前世,便是行知先生青幼年时期的苦难生活,没有那份苦难,他是断然无法驭写出如此充溢着悲悯的文字;这篇文章的当下,便是行知先生对“自由”“平等”等恒久信条的奋然高蹈与竭力呼唤;这篇文章的未来,便是行知先生将自己的后半生交付给整个国家与民族的碌碌身影与重重足迹。
二
行知先生是走过抗战烽火的。在国危民难的关头,他终究没有忘却一份教育者的本心与担当。我们可以断言:当一颗执着的教育心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