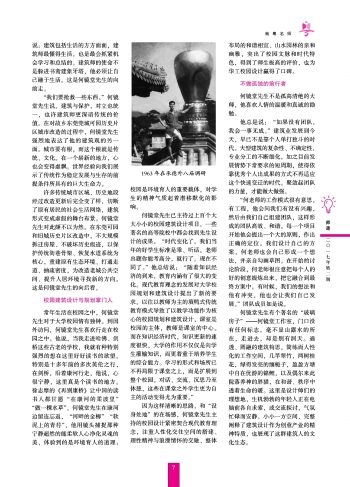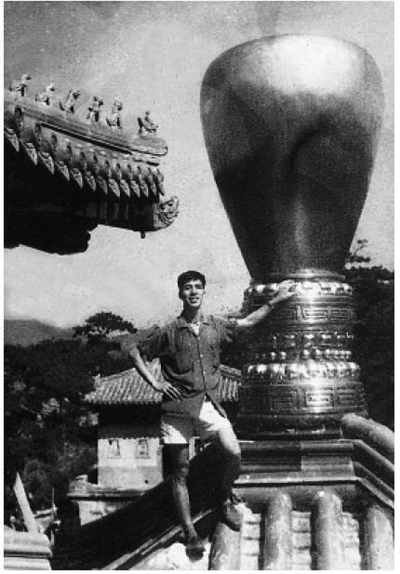“我们要抢救一些东西。”何镜堂先生说。建筑与保护,对立也统一,也许建筑师更深谙传统的价值。在对故乡东莞莞城可园历史片区城市改造的过程中,何镜堂先生强烈地表达了他的建筑观的另一面。城市要有根,而这个根就是传统、文化。在一个崭新的地方,心也会变得虚飘。世界经验向我们展示了传统作为稳定发展与生存的前提条件所具有的巨大生命力。
许多传统城市区域、历史地段经过改造更新后完全变了样,切断了原有居民的社会生活网络,建筑形式变成虚假的舞台布景。何镜堂先生对此颇不以为然。在东莞可园和旧城历史片区改造中,不大规模拆迁房屋、不破坏历史痕迹,以保护传统街巷骨架、恢复水道系统为核心,重建原有生态环境、打通走道、抽疏密度,为改造老城公共空间、提升人居环境寻找新的方向。这是何镜堂先生的向后看。
校园建筑设计与规划掌门人
常年生活在校园之中,何镜堂先生对于大学校园情有独钟。到国外访问,何镜堂先生喜欢行走在校园之中。他说,当我走进哈佛、剑桥这些古老的学校,我就有种特别强烈的想在这里好好读书的欲望。特别是十多年前的多次英伦之行,在剑桥,沿着康河行走,他说,心很宁静,这里真是个读书的地方。徐志摩的《再别康桥》让中国的读书人都甘愿“在康河的柔波里”“做一棵水草”。何镜堂先生在康河边留连忘返,“河畔的金柳”“软泥上的青荇”,他用镜头捕捉那种宁静超然的能柔软人心净化灵魂的美,体验到的是环境育人的道理:校园是环境育人的重要载体,对学生的精神气质起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何镜堂先生已主持过上百个大大小小的校园建筑设计项目,一些著名的高等院校中都会找到先生设计的成果。“时代变化了。我们当年的好学生标准是乖、听话,老师出题你能考高分,就行了。现在不同了。”他总结说:“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教育内涵有了很大的变化。现代教育理念的发展对大学校园规划和建筑设计提出了新的要求。以往以教师为主的填鸭式传统教育模式导致了以教学功能作为核心的校园规划和建筑设计,课室是校园的主体,教师是课室的中心。而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更新的速度很快,大学的作用不仅仅是向学生灌输知识,而更着重于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学习的形式和场所已不再局限于课堂之上,而是扩展到整个校园。对话、交流、沉思乃至休憩,这些在课堂之外学生更为自主的活动变得尤为重要。”
因为这样清晰的思路,和“设身处地”的在场感,何镜堂先生主持的校园设计紧密契合现代教育理念,注重人性化交往空间的搭建、理性精神与浪漫情怀的交融、整体布局的和谐相宜、山水园林的亲和幽雅,突出了校园文脉和时代特色,得到了师生极高的评价,也为华工校园设计赢得了口碑。
不做孤独的前行者
何镜堂先生不是孤高清绝的大师,他喜欢人情的温暖和真诚的勖勉。
他总是说:“如果没有团队,我会一事无成。”建筑业发展到今天,早已不是靠个人单打独斗的时代。大型建筑的复杂性、不确定性,专业分工的不断细化,加之目前发展情势下常要求的短周期,使得依靠优秀个人出成果的方式不再适应这个快速变迁的时代。聚敛起团队的力量,才能做大做强。
“何老师的工作模式很有意思,有工程,他会问我们有没有兴趣,然后由我们自己组建团队,这样形成的团队高效、和谐。每一个项目开始他会提出一个大的原则,作出正确的定位。我们设计自己的方案,何老师也会自己形成一个想法,并亲自勾画草图。在开始的讨论阶段,何老师很注意把每个人的好的创意提炼出来,把它融合到最终方案中。有时候,我们的想法和他有冲突,他也会让我们自己发展。”团队成员如是说。
何镜堂先生有个著名的“玻璃房子”——何镜堂工作室,门口没有任何标志,毫不显山露水的所在,走进去,却是别有洞天。通透、圆融的建筑构思,简练而人性化的工作空间,几竿翠竹,两树桂花,绿得发亮的缅栀子,盈盈方塘中自在优游的锦鲤,以及偶尔来此院落养神的胖猫,在和谐、秩序中透着生命的暖。这里是设计师们的理想地,生机勃勃的年轻人正在电脑前各自求索,或交流探讨,气氛忙碌而安静。小小一方空间,完整阐释了建筑设计作为创意产业的精神特质,也展现了这群建筑人的文化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