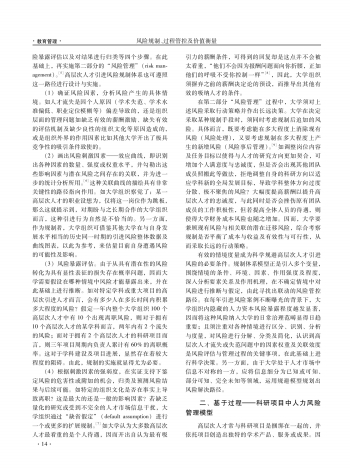(1)确证风险因素,分析风险产生的具体情境。如人才流失是因个人原因(学术失范、学术水准偏低、职业定位模糊等)偏差导致的,还是组织层面的管理问题如缺乏有效的薪酬激励、缺失有效的评估机制及缺少良性的组织文化等原因造成的,或是组织外界的作用因素比如其他大学开出了极具竞争性的吸引条件致使的。
(2)画出风险刺激因素——效应曲线,即识别出各种因素的数量、强度或权重水平,并勾勒出这些影响因素与潜在风险之间存在的关联,并为进一步的统计分析所用。[6]这种关联曲线的描绘具有非常关键性的路径指向作用。如大学组织察觉了:某一高层次人才的职业设想为,仅将这一岗位作为跳板,那么这就提示到,对期盼与之长期合作的大学组织而言,这种引进行为自然是不恰当的。另一方面,作为规制者,大学组织可借鉴其他大学在与自身发展水平相当的历史同一时期的引进风险整体数据及曲线图表,以此为参考,来估量目前自身遭遇风险的可能性及影响。
(3)风险暴露评估。由于从具有潜在性的风险转化为具有显性表征的损失存在概率问题,因而大学需要假设在哪种情境中风险才能暴露出来,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推断。如对特定学科或重大项目的高层次引进人才而言,会有多少人在多长时间内积累多大程度的风险?假定一年内整个大学组织100个高层次人才中有10个出现离职风险,则对于拥有10个高层次人才的某学科而言,两年内有2个流失的风险;而对于拥有2个高层次人才的科研项目而言,则三年项目周期内负责人累计有60%的离职概率。这对于学科建设及项目进展,显然存在着较大程度的阻碍。由此,规制的实施就显得尤为必要。
(4)根据刺激因素的强弱度,在实证支持下鉴定风险的危害性或附加的机会,归类及预测风险结果与后续可能。如特定的组织文化是否在事实上导致离职?这是最大的还是一般的影响因素?若缺乏量化的研究或受到不完全的人才市场信息干扰,大学组织通过“缺省假定”(default assumption)进行一个或更多的扩展规制。[7]如大学认为大多数高层次人才最看重的是个人待遇,因而开出自认为最有吸引力的薪酬条件,可得到的回复却是这点并不会被太看重,“他们不会因为报酬问题而向你折腰,正如他们的呼吸不受你控制一样”[8],因此,大学组织须摒弃之前的薪酬决定论的预设,而推导出其他有效的吸纳人才的条件。
在第二部分“风险管理”过程中,大学须对上述风险采取行动策略并作出长远决策。大学在决定采取某种规制手段时,须同时考虑规制后追加的风险。具体而言,既要考虑能在多大程度上消除现有风险(风险处理),又要考虑规制在多大程度上产生的新增风险(风险事后管理)。[9]如调整岗位内容及任务目标以使得与人才的研究方向更加契合,可增加个人满意度与忠诚度,但是否会出现其他团队成员照搬此等做法,拒绝调整自身的科研方向以适应学科新的全局发展目标,导致学科整体方向过度分散、极不聚焦的风险?大幅度提高薪酬以提升高层次人才的忠诚度,与此同时是否会挫伤原有团队成员的工作积极性,但若提高全体人员的待遇,则使得大学财务成本风险也随之增加。因而,大学要兼顾现有风险与相关联的潜在迁移风险,综合考察规制是否平衡了成本与收益及有效性与可行性,从而采取长远的行动策略。
·教育管理·风险规制、过程管控及价值衡量有效的情境度量成为科学规避高层次人才引进风险的必要条件。规制体系模型正是引入多个变量,围绕情境的条件、环境、因素、作用强度及程度,深入分析要素关系及作用机理,在不确定情境中对风险进行推断与假定,由此寻找出联动的风险管控路径。在每年引进风险案例不断曝光的背景下,大学组织内隐藏的人力资本风险暴露程度越发显著,因而将这种风险纳入大学的日常治理范畴显得日趋重要;且须注重对各种情境进行区分、识别、分析与度量,对风险进行分解、分类及简化,认识到高层次人才流失或失范问题中的因素权重及关联效度是风险评估与管理过程的关键事项,在此基础上进行科学决策。另一方面,由于大学处于人才市场中信息不对称的一方,应将信息细分为已知或可知、部分可知、完全未知等领域,运用规避模型规划出风险解决路径。
二、基于过程——科研项目中人力风险管理模型
高层次人才常与科研项目是捆绑在一起的,并依托项目创造出独特的学术产品、服务或成果。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