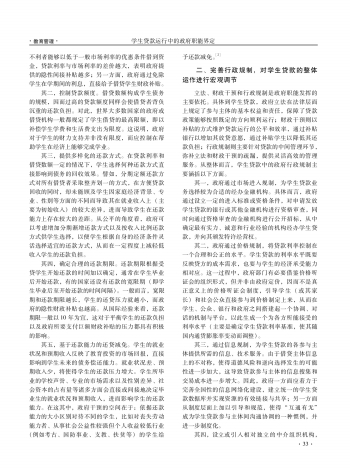其二,控制贷款额度。借贷数额构成学生债务的规模,因而过高的贷款额度同样会使借贷者背负沉重的还款负担。对此,世界大多数国家的政府或借贷机构一般都规定了学生借贷的最高限额,即以补偿学生学费和生活费支出为限度。这说明,政府对于学生的财力支持并非没有限度,而应控制在帮助学生在经济上能够完成学业。
其三,提供多样化的还款方式。在贷款利率和借贷数额一定的情况下,学生选择何种还款方式直接影响到债务的回收效果。譬如,分期定额还款方式对所有借贷者采取整齐划一的方式,在方便贷款回收的同时,却未能顾及学生因家庭经济背景、专业、性别等方面的不同而导致其在就业收入上(主要为初始收入)的较大差异,进而导致学生在还款能力上存在较大的差距。从公平的角度看,政府可以考虑增加分期渐增还款方式以及按收入比例还款方式供学生选择,以便学生根据自身的经济条件灵活选择适宜的还款方式,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低收入学生的还款负担。
其四,确定合理的还款期限。还款期限根据受贷学生开始还款的时间加以确定,通常在学生毕业后开始还款,有的国家还设有还款的宽限期(即学生毕业后至开始还款的时间间隔)。一般而言,宽限期和还款期限越长,学生的还贷压力就越小,而政府的隐性财政补贴也越高。从国际经验来看,还款期限一般以10年为宜,这对于平衡学生的还款负担以及政府所要支付巨额财政补贴的压力都具有积极的影响。
其五,基于还款能力的还贷减免。学生的就业状况和预期收入反映了教育投资的市场回报,直接影响到学生未来的债务偿还能力。就业状况差、预期收入少,将使得学生的还款压力增大。学生所毕业的学校声誉、专业的市场需求以及性别差异、社会资本的占有量等诸多方面会直接或间接地决定毕业生的就业状况和预期收入,进而影响学生的还款能力。在这其中,政府干预的空间在于:依据还款能力的大小区别对待不同的学生,比如对丧失劳动能力者、从事社会公益性较强但个人收益较低行业(例如考古、国防事业、支教、扶贫等)的学生给予还款减免。[2]
二、完善行政规制,对学生贷款的整体运作进行宏观调节立法、财政干预和行政规制是政府职能发挥的主要依托。具体到学生贷款,政府立法在法律层面上规定了参与主体的基本权益和责任,保障了贷款政策能够按照既定的方向顺利运行;财政干预则以补贴的方式维护贷款运行的公平和效率,通过补贴银行以增加其放贷意愿,通过补贴学生以降低其还款负担;行政规制则主要针对贷款的中间管理环节,弥补立法和财政干预的疏漏,提供灵活高效的管理服务。从整体而言,学生贷款中的政府行政规制主要涵括以下方面。
其一,政府通过市场进入规制,为学生贷款业务选择较为合适的经办金融机构。具体而言,政府通过设立一定的进入标准或资格条件,对申请发放学生贷款的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进行资格审查,同时向通过资格审查的金融机构进行公开招标,从中确定最有实力、诚意和行业经验的机构经办学生贷款,并向其颁发特许经营权。
其二,政府通过价格规制,将贷款利率控制在一个合理和公正的水平。学生贷款的利率水平既要反映贷方的成本需求,也要与学生的经济承受能力相对应。这一过程中,政府部门有必要借鉴价格听证会的组织形式,但并非由政府定价,因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价格听证会制度,引导学生(或其家长)和社会公众直接参与到价格制定上来,从而在学生、公众、银行和政府之间搭建起一个协调、对话的机制与平台,以此生成一个为各方所能接受的利率水平(主要是确定学生贷款利率基准,使其随国内通货膨胀率变动而调整)。
其三,通过信息规制,为学生贷款的各参与主体提供所需的信息、技术服务。由于借贷主体信息上的不对称,使得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发生的可能性进一步加大,这导致贷款参与主体的信息搜集和交易成本进一步增大。因此,政府一方面应着力于完善全国性的信息网络化建设,建立统一的学生贷款数据库并实现资源的有效链接与共享;另一方面从制度层面上加以引导和规范,使得“互通有无”成为学生贷款参与主体间沟通协调的一种惯例,并进一步制度化。
其四,设立或引入相对独立的中介组织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