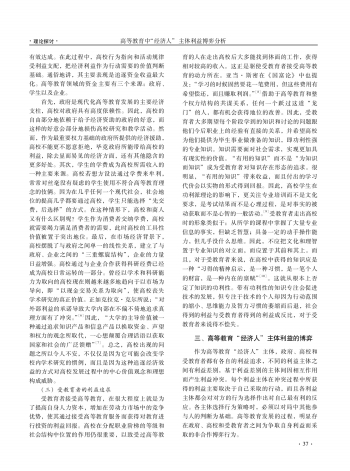首先,政府是现代化高等教育发展的主要经济支柱,高校对政府具有高度依赖性。因此,高校的自由部分地依赖于给予经济资助的政府的好意,而这样的好意会部分地损伤高校研究和教学活动。然而,作为最重要权力基础的政府所提供的经济援助,高校不能更不愿意拒绝,毕竟政府所能带给高校的利益,除去显而易见的经济方面,还有其他隐含的更多好处。其次,学生的学费成为高校所需收入的一种主要来源。高校若想方设法通过学费来牟利,常常对丝毫没有疑虑的学生使用不符合高等教育理念的伎俩。因为在几乎任何一个现代社会,社会地位的提高几乎都要通过高校,学生只能选择“先交费,后选择”的方式。在这种情形下,高校和商人又有什么区别呢?学生作为消费者交纳学费,高校就需要竭力满足消费者的需要,此时高校的工具性价值被置于突出地位。最后,在市场经济背景下,高校摆脱了与政府之间单一的线性关系,建立了与政府、企业之间的“三重螺旋结构”,企业的力量日益增强。高校通过与企业合作获得科研经费已经成为高校日常运转的一部分。曾经以学术和科研能力为取向的高校现在则越来越多地趋向于以市场为导向,即“以现金交易关系为取向”,使高校丧失学术研究的真正价值。正如克拉克·克尔所说:“对外部利益的承诺导致大学内部在不偏不倚地追求真理方面有了冲突。”[6]因此,“大学的主导价值被一种通过追求知识产品和信息产品以换取资金、声望和权力的观念所取代,一心想颠覆合理话语以获取国家和社会的广泛馈赠”[7]。总之,高校出现的问题之所以令人不安,不仅仅是因为它可能会改变学校内学术研究的惯例,而且是因为这种追逐经济效益的方式对高校发展过程中的中心价值观念和理想构成威胁。
(三)受教育者的利益追求
受教育者接受高等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提高自身人力资本,增加在劳动力市场中的竞争优势,使其通过接受高等教育服务而获得对教育进行投资的利益回报。高校在分配职业阶梯的等级和社会结构中位置的作用仍很重要,以致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在走出高校后大多能找到体面的工作,获得相对较高的收入。这正是驱使受教育者接受高等教育的动力所在。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也提及:“学习的时候固然要花一笔费用,但这些费用有希望偿还,而且赚取利润。”[8]借助于高等教育和整个权力结构的共谋关系,任何一个跃过这道“龙门”的人,都有机会获得地位的改善。因此,受教育者大多期望每个阶段学到的知识和讨论的问题跟他们今后职业上的经验有直接的关系,并希望高校为他们提供为毕生事业做准备的知识,即功利性强的专业知识。知识需要面对社会需求,实现更加具有现实性的价值。“有用的知识”而不是“为知识而知识”成为受教育者对知识存在形态的追求。很明显,“有用的知识”带来收益,而且付出的学习代价会以实物的形式得到回报。因此,高校学生在功利派理论的影响下,更关注专业培训而不是文化要求,是考试结果而不是心理过程,是对事实的被动获取而不是心智的一般活动。[9]受教育者走出高校时的形象类似于:从所学的课程中掌握了大量专业信息的事实,但缺乏智慧;具备一定的动手操作能力,但几乎没什么思维。因此,不应把文化和理智置于专业知识的对立面,而应置于其前和其上。而且,对于受教育者来说,在高校中获得的知识应是一种“习得的精神启示,是一种习惯,是一笔个人的财富,是一种内在的禀赋”[10]。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知识的功利性。带有功利性的知识专注会促进技术的发展,但专注于技术的个人却因为行动范围的缩小、思维能力及智力习惯的萎缩而后退,社会得到的利益与受教育者得到的利益成反比,对于受教育者来说得不偿失。
三、高等教育“经济人”主体利益的博弈
作为高等教育“经济人”主体,政府、高校和受教育者都有各自的利益追求,不同的利益主体之间有利益差别,基于利益差别的主体间因相互作用而产生利益冲突。每个利益主体在冲突过程中所获得的利益主要取决于自己采取的行动,而且各利益主体都会对对方的行为选择作出对自己最有利的反应。各主体选择行为策略时,必须以对局中其他参与人的判断为基础。高等教育发展的过程,明显存在政府、高校和受教育者之间为争取自身利益而采取的非合作博弈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