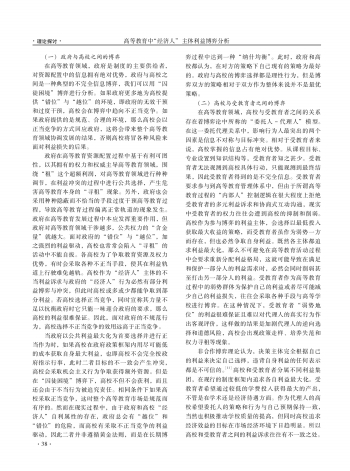在高等教育领域,政府是制度的主要供给者,对资源配置中的信息拥有绝对优势,政府与高校之间是一种典型的不完全信息博弈,我们可以用“囚徒困境”博弈进行分析。如果政府更多地为高校提供“错位”与“越位”的环境,即政府的无效干预和过度干预,高校会在博弈中趋向不正当竞争。如果政府提供的是规范、合理的环境,那么高校会以正当竞争的方式回应政府,这将会带来整个高等教育领域协调发展的结果,否则高校将冒各种风险来面对利益损失的后果。
政府在高等教育资源配置过程中基于有利可图性,以其拥有的权力和权威主导高等教育领域,围绕“租”这个超额利润,对高等教育领域进行种种调节,在利益冲突的过程中进行公共选择,产生危害高等教育本身的“寻租”现象。另外,政府也会采用种种隐蔽而不恰当的手段过度干预高等教育过程,导致高等教育过程偏离正常轨道的现象发生。政府在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本应发挥重要作用,但政府对高等教育领域干涉越多,公共权力的“含金量”就越大。面对政府的“错位”与“越位”,加之强烈的利益驱动,高校也常常会陷入“寻租”的活动中不能自拔。各高校为了争取教育资源及权力优势,有时会采取各种不正当手段,使其在利益轨道上行驶难免越轨。高校作为“经济人”主体的不当利益诉求与政府的“经济人”行为必然有部分利益博弈与冲突,但此时高校或多或少都能争取到部分利益。若高校选择正当竞争,同时宣称其力量不足以抗衡政府时它只能一味迎合政府的要求,那么高校的利益很难保证。因此,面对政府的不规范行为,高校选择不正当竞争的效用远高于正当竞争。
当政府以公共利益最大化为首要选择并进行正当作为时,如果高校在政府政策框架内用尽可能低的成本获取自身最大利益,也即高校不会完全按政府指示行事,此时二者目标的不一致会产生冲突,高校会采取机会主义行为争取获得额外资源。但是在“囚徒困境”博弈下,高校不但不会获利,而且还会由于不当行为被追究责任。相同条件下如果高校采取正当竞争,这时整个高等教育市场是规范而有序的。然而在现实过程中,由于政府和高校“经济人”自利属性的存在,政府总会有“越位”和“错位”的危险,而高校有采取不正当竞争的利益驱动,因此二者并非遵循黄金法则,而是在长期博弈过程中达到一种“纳什均衡”。此时,政府和高校都认为,在对方的策略下自己现有的策略为最好的。政府与高校的博弈选择都是理性行为,但是博弈双方的策略相对于双方作为整体来说并不是最优策略。
(二)高校与受教育者之间的博弈
在高等教育领域,高校与受教育者之间的关系存在着博弈论中所称的“委托人-代理人”模型。在这一委托代理关系中,影响行为人最突出的两个因素是信息不对称与目标冲突。相对于受教育者来说,高校掌握的信息占有绝对优势。从课程目标、专业设置到知识结构等,受教育者知之甚少。受教育者无法观测到高校具体行动,只能观测到最终结果,因此受教育者得到的是不完全信息。受教育者要求参与到高等教育管理体系中,但由于所谓高等教育过程的“内部人”控制逻辑在很大程度上拒绝受教育者的多元利益诉求和协商式互动沟通,现实中受教育者的权力往往会遭到高校的抑制和削弱。高校作为参与博弈的利益主体,会选择以最低投入获取最大收益的策略,而受教育者虽作为弱势一方而存在,但也必然争取自身利益。既然各主体都追求利益最大化,那么不可避免在高等教育活动过程中会要求重新分配利益格局,这就可能导致在满足和保护一部分人的利益需求时,必然会同时削弱甚至打击另一部分人的利益。受教育者作为高等教育过程中的弱势群体为保护自己的利益或者尽可能减少自己的利益损失,往往会采取各种手段与高等学校进行博弈。在这种情况下,受教育者“弱势地位”的利益很难保证且难以对代理人的真实行为作出客观评价,这样做的结果是加剧代理人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高校会出现政策走样、培养失范和权力寻租等现象。
非合作博弈理论认为,决策主体完全根据自己的利益来决定自己选择,违背自身利益的任何表示都是不可信的。[11]高校和受教育者分属不同利益集团,在现行的制度框架内追求各自利益最大化。受教育者希望通过较低的学费投入获得最大的产出,不管是在学术还是经济待遇方面。作为代理人的高校希望委托人的策略和行为与自己预期保持一致,当然也积极推动学校质量的提高,但同时高校追求经济效益的目标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日趋明显。所以高校和受教育者之间的利益诉求往往有不一致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