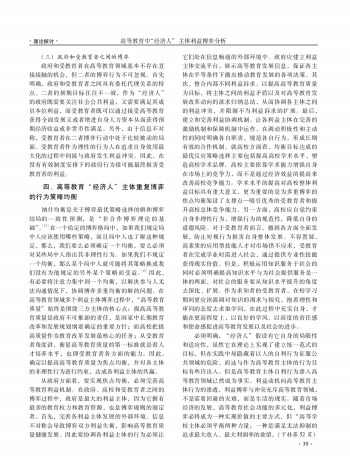政府和受教育者在高等教育领域基本不存在直接接触的机会,但二者的博弈行为不可忽视。首先明确,政府和受教育者之间具有委托代理关系的特点。二者的预期目标往往不一致,作为“经济人”的政府既需要关注社会公共利益,又需要满足其成员本位利益,而受教育者既可以通过接受高等教育获得全面发展又或者增进自身人力资本从而获得预期经济收益或非货币性满足。另外,由于信息不对称,受教育者在二者博弈行动中处于比较被动的局面。受教育者作为理性的行为人在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过程中间接与政府发生利益冲突。因此,在没有有效制度安排下的政府行为很可能最终损害受教育者的利益。
四、高等教育“经济人”主体重复博弈的行为策略均衡纳什均衡是关于博弈最优策略选择的解和博弈结局的一致性预测,是“非合作博弈理论的基础”。[12]在一个给定的博弈格局中,如果我们规定局中人应该使用哪些策略,而且局中人也了解这种规定,那么,我们要么必须确定一个均衡,要么必须对某些局中人指出其非理性行为。如果我们不规定一个均衡,那么某个局中人就可能将其策略换成我们没有为他规定的另外某个策略而受益。[13]因此,有必要将注意力集中到一个均衡,以解决参与人无法沟通情况下,协调博弈多重均衡的解的问题。在高等教育领域多个利益主体博弈过程中,“高等教育质量”始终是围绕三方主体的核心点: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是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是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确定的重要方针;而高校把提高质量作为教育改革发展最核心的任务;从受教育者角度讲,衡量高等教育质量的第一标准就是看人才培养水平,也即受教育者各方面的能力。因此,确定以提高高等教育质量为焦点均衡,并对各主体的非理性行为进行约束,达成各利益主体的共赢。
从政府方面看,要实现焦点均衡,必须完善高等教育利益机制。在政府、高校和受教育者之间的博弈过程中,政府是最大的利益主体,因为它握有最多的教育权力和教育资源,也是博弈规则的制定者。首先,完善各利益主体发展的外部环境。信息不对称会导致博弈双方利益失衡,影响高等教育质量健康发展。因此要协调各利益主体的行为必须让它们处在信息畅通的外部环境中。政府应建立利益主体交流平台,展示高等教育发展信息,保证各主体在平等条件下做出推动教育发展的各项决策。其次,整合内部不同利益诉求。以提高高等教育质量为目标,将主体之间的利益矛盾以及对高等教育发展改革动向的欲求归纳总结,从而协调各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并限制不当利益诉求的扩展。最后,建立和完善利益协调机制。让各利益主体在完善的激励机制和保障机制中运作,在调动积极性和主动性的同时明确各自职责,规范各自行为,形成长期有效的合作机制。就高校方面看,均衡目标达成的最优反应策略选择主要包括提高高校学术水平,塑造高校学术品牌。高校主要依靠学术能力增强自身在市场上的竞争力,而不是通过经济效益的提高来改善高校竞争能力。学术水平的提高对高校整体利益目标具有重大意义,更为重要的是为多重博弈的焦点均衡架设了支撑点—吸引优秀的受教育者和提升高校总体竞争能力。另一方面,高校应自觉约束自身非理性行为,增强行为的规范性,降低自身的道德风险。对于受教育者而言,做到各方面全面发展,防止短视行为损害自身整体发展。不容置疑,高素质的应用型技能人才对市场供不应求,受教育者在完成学业时需进入社会,通过提供专业性技能获得现实价值。但是,积极运用知识服务于社会的同时必须明确提高知识水平与为社会提供服务是一体的两面,对社会的服务要从知识水平提升的角度去深化、扩展。作为求知者的受教育者,在校学习期间更应该强调对知识的渴求与探究,抱着理性和审问的态度去求取学问,在此过程中充实自身,才能在更高程度上,以良好的学风、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促进高等教育发展以及社会的进步。
必须明确,“经济人”假设有它自身的局限性和适应性,虽然它在理论上实现了建立统一范式的目标,但在实践中却隐藏着以人的自利行为征服公共领域的危险,而这与作为高等教育主体的行为目标有些许出入。但是高等教育主体自利行为渗入高等教育领域已然成为事实。利益动机向高等教育主体行为的渗透,利益博弈与冲突充斥高等教育领域,不是需要回避的灾难,而是生活的现实。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高等教育社会功能的多元化,利益博弈必将成为一种实现价值的主要方式,但“高等学校主体必须平衡两种力量:一种是满足无法抑制的追求最大收入、最大利润率的欲望,(下转第5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