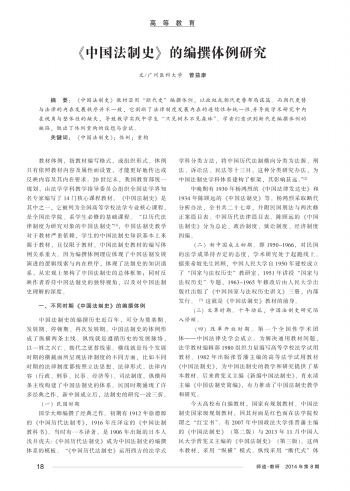摘要:《中国法制史》教材沿用“断代史”编撰体例,以政权或朝代更替布局谋篇。而朝代更替与法律的内在发展秩序并不一致,它割断了法律制度发展内在的连续性和统一性,并导致学术研究中内在视角与整体性的缺失,导致教学实践中学生“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学者们意识到断代史编撰体例的缺陷,做出了体例重构的设想与尝试。
关键词:《中国法制史》;体例;重构
教材体例,指教材编写格式,或组织形式。体例只有依照教材内容及属性而设置,才能更好地传达或反映内容及其内在要求。20世纪末,我国教育部统一规划,由法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组织全国法学界知名专家编写了14门核心课程教材。《中国法制史》是其中之一,它被列为全国高等学校法学专业核心课程,是全国法学院、系学生必修的基础课程。“以历代法律制度为研究对象的中国法制史”[1],中国法制史教学对于教材严重依赖,学生的中国法制史知识基本上来源于教材,且仅限于教材。中国法制史教材的编写体例关系重大。因为编撰体例理应体现了中国法制发展演进的逻辑线索与内在秩序,体现了法制史的知识谱系,从宏观上架构了中国法制史的总体框架;同时反映作者看待中国法制史的独特视角,以及对中国法制史理解的深度。
一、不同时期《中国法制史》的编撰体例
中国法制史的编撰历史近百年,可分为奠基期、发展期、停顿期、再次发展期。中国法制史的体例形成了纵横两条主线。纵线就是遵循历史的发展脉络,以一姓之兴亡、朝代之更替线索。横线就是每个发展时期的横截面所呈现法律制度的不同方面,比如不同时期的法律制度都按照立法思想、法律形式、法律内容(行政、刑事、民事、经济等)、司法制度。纵横两条主线构建了中国法制史的体系。民国时期涌现了许多经典之作,新中国成立后,法制史的研究一波三折。
(一)民国时期
国学大师编撰了经典之作。初期有1912年徐德源的《中国历代法制考》,1916年庄泽定的《中国法制教科书》。当时有一本译著,是1906年出版的日本人浅井虎夫:《中国历代法制史》成为中国法制史的编撰体系的模板。“《中国历代法制史》运用西方的法学式学科分类方法,将中国历代法制横向分类为法源、刑法、诉讼法、民法等十三目,这种分类研究办法,为中国法制史学科体系建构了框架,其影响甚远。”[2]
中晚期有1930年杨鸿烈的《中国法律发达史》和1934年陈顾远的《中国法制史》等。杨鸿烈采取断代分析办法,全书共二十七章,并附民国刑法与两次修正案篇目表、中国历代法律篇目表。陈顾远的《中国法制史》分为总论、政治制度、狱讼制度、经济制度四编。
(二)新中国成立初期。即1950-1966,对民国的法学成果持否定的态度,学术研究处于起跑线上。据张希坡先生回顾,中国人民大学自1950年建校成立了“国家与法权历史”教研室,1951年讲授“国家与法权历史”专题,1963-1965年修改后由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国家与法权历史讲义》三册,内部发行。[3]这就是《中国法制史》教材的前身。
(三)文革时期。十年动乱,中国法制史研究陷入停顿。
(四)改革开放时期。第一个全国性学术团体——中国法律史学会成立。为解决通用教材问题,法学教材编辑部1980组织力量编写高等学校法学试用教材。1982年出版张晋藩主编的高等法学试用教材《中国法制史》,为中国法制史的教学和研究提供了基本教材。后来曾宪义主编《新编中国法制史》、肖永清主编《中国法制史简编》,有力推动了中国法制史教学和研究。
今天高校有自编教材,国家有规划教材。中国法制史国家级规划教材,因其封面是红色而在法学院校谓之“红宝书”。有2007年中国政法大学张晋藩主编的《中国法制史》(第二版)与2013年11月中国人民大学曾宪义主编的《中国法制史》(第三版)。这两本教材,采用“纵横”模式。纵线采用“断代式”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