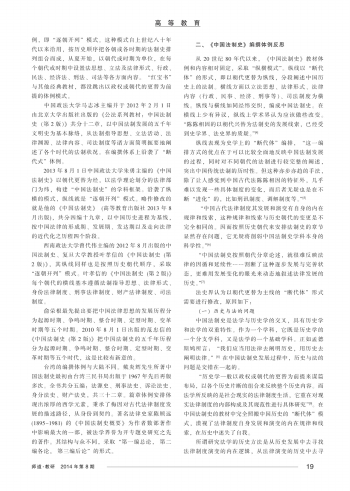中国政法大学马志冰主编并于2012年2月1日 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公法系列教材:中国法制史(第2版)》共分十二章,以中国法制发展的五千年文明史为基本脉络,从法制指导思想、立法活动、法律渊源、法律内容、司法制度等诸方面简明扼要地阐述了各个时代的法制状况。在编撰体系上沿袭了“断代式”体例。
2013年8月1日中国政法大学朱勇主编的《中国法制史》以朝代更替为经,以法学理论划分的法律部门为纬,构建“中国法制史”的学科框架。沿袭了纵横的模式,纵线就是“逐朝开列”模式。略作修改的就是他的《中国法制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年8月出版),共分四编十九章,以中国历史进程为基线,按中国法律的形成期、发展期、发达期以及走向法律的近代化之历程四个阶段。
西南政法大学曾代伟主编的2012年8月出版的中国法制史、复旦大学教授叶孝信的《中国法制史(第2版)》,其纵线同样也是按照历史朝代顺序,采取“逐朝开列”模式。叶孝信的《中国法制史(第2版)》每个朝代的横线基本遵循法制指导思想、法律形式、身份法律制度、刑事法律制度、财产法律制度、司法制度。
俞荣根最先提出要把中国法律思想的发展历程分为起源时期、争鸣时期、整合时期、定型时期、变革时期等五个时期。2010年8月1日出版的范忠信的《中国法制史(第2版)》把中国法制史的五千年历程分为起源时期、争鸣时期、整合时期、定型时期、变革时期等五个时代,这是比较有新意的。
台湾的编撰体例与大陆不同。戴炎辉先生所著中国法制史最初由台湾三民书局出版于1967年先后再版多次。全书共分五编:法源史、刑事法史、诉讼法史、身分法史、财产法史,共三十二章。篇章体例安排体现出浓厚的西学元素,秉承了梅因对古代法律制度发展的描述路径,从身份到契约。著名法律史家陈顾远(1895-1981)的《中国法制史概要》为作者数部著作中影响最大的一部,被法学界誉为开专题史研究之先的著作。其结构与众不同,采取“第一编总论, 第二编各论, 第三编后论”的形式。
二、《中国法制史》编撰体例反思
从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中国法制史》教材体例和内容相对固定,采取“纵横模式”。纵线以“断代体”的形式,即以朝代更替为纵线,分段阐述中国历史上的法制。横线方面以立法思想、法律形式、法律内容(行政、民事、经济、刑事等)、司法制度为横线。纵线与横线如同经纬交织,编成中国法制史。在横线上少有异议,纵线上学术界认为应该做些改变。“陈陈相因的以朝代兴替为法制史的发展线索,已经受到史学界、法史界的质疑。”[4]
纵线表现为史学上的“断代体”编排,“这一编排方式的优点在于可以比较全面地反映中国法制发展的过程,同时对不同朝代的法制进行较完整的阐述,突出中国传统法制的历时性。但这种亦步亦趋的手法,除了让人感觉到中国古代法陈陈相因的特征外,几乎难以发现一些具体制度的变化,而后者无疑也是在不断“进化”的,比如刑讯制度、调解制度等。”[5]
“中国古代法律制度其发展和演变有自身的内在规律和线索,这种规律和线索与历史朝代的变更是不完全相同的。因而按照历史朝代来安排法制史的章节显然存在问题,它无疑将削弱中国法制史学科本身的科学性。”[6]
“中国法制史按照朝代分章论述,就很难反映法律的因循和延续性……割断了这种逐步发展与完善状态,更难用发展变化的眼光来动态地叙述法律发展的历史。”[7]
法史界认为以朝代更替为主线的“断代体”形式需要进行修改,原因如下:
(一)历史与法的问题
中国法制史是法学与历史学的交叉,具有历史学和法学的双重特性。作为一个学科,它既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又是法学的一个基础学科。正如孟德斯鸠所言:“我们应当用法律去阐明历史,用历史去阐明法律。”[8]在中国法制史发展过程中,历史与法的问题是交错在一起的。
“历史学一般以政权或朝代的更替为前提来谋篇布局,以各个历史片断的组合来反映整个历史内容。而法学所反映的是社会现实的法律制度生活,它重在对现实法律制度的内部构成及其规范性进行具体研究”[9]。在中国法制史的教材中完全照搬中国历史的“断代体”模式,漠视了法律制度自身发展和演变的内在规律和线索,在历史中迷失了自我。
所谓研究法学的历史方法是从历史发展中去寻找法律制度演变的内在逻辑,从法律演变的历史中去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