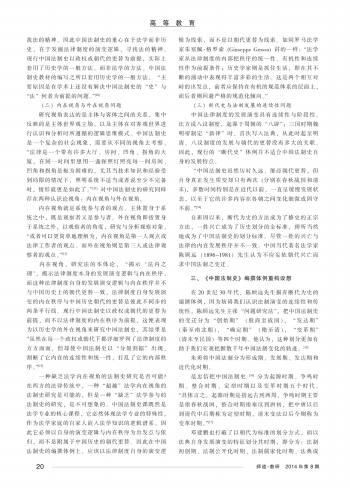(二)内在视角与外在视角问题
研究视角表达的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集中反映的是主体世界观立场,以及主体在对客观世界进行认识和分析时所遵循的逻辑思维模式。中国法制史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现象,需要从不同的视角去考察。“法律是一个带有许多大厅、房间、凹角、拐角的大厦,在同一时间里想用一盏探照灯照亮每一间房间、凹角和拐角是极为困难的,尤其当技术知识和经验受到局限的情况下,照明系统不适当或者说至少不完备时,情形就更是如此了。”[11]对中国法制史的研究同样存在两种认识论视角:内在视角与外在视角。
内在视角就是系统参与者的观点。主体置身于系统之中,既是观察者又是参与者。外在视角即指置身于系统之外,以观察者的角度,研究与分析观察对象。“或者可以更简单地理解为,内在视角是第一人观点或法律工作者的观点。而外在视角则是第三人或法律观察者的观点。”[12]
内在视角,研究法的本体论,“揭示‘法内之理’,揭示法律制度本身的发展演变逻辑与内在秩序。而这种法律制度自身的发展演变逻辑与内在秩序并不与中国历史上的朝代更替一致,法律制度自身发展演变的内在秩序与中国历史朝代的更替是彼此不同步的两条平行线。现行中国法制史以政权或朝代的更替为前提,而不以法律制度的内在秩序为前提,这便表现为以历史学的外在视角来研究中国法制史,其结果是“虽然在每一个政权或朝代下都详细罗列了法律制度的方方面面,但却使中国法制史以“分裂割据”出现,割断了它内在的连续性和统一性,打乱了它的内部秩序。”[13]
一种缺乏法学内在视角的法制史研究是否可能? 在西方的法律传统中,一种“超越”法学内在视角的法制史研究是可能的,但是一种“缺乏”法学参与的法制史的研究,是不可想象的。中国法制史课既然是法学专业的核心课程,它必然体现法学专业的特殊性,作为法学家庭的自家人嵌入法学知识的逻辑谱系。因此它必须以自身的演变逻辑与内在秩序为出发点与依归,而不是附属于中国历史的朝代更替。因此在中国法制史的编撰体例上,应该以法律制度自身的演变逻辑为线索,而不是以朝代更替为线索。如同罗马法学家朱塞佩·格罗索(Giuseppe Grosso)讲的一样:“法学家从法律制度的内部把秩序的统一性、有机性和连续性作为前提条件;历史学家则是抓住生活,即在其不断的涌动中表现得丰富多彩的生活。这是两个相互对峙的出发点,前者应保持在有机的规范体系的层面上,而后者则回避严格的规范化倾向。”
(三)断代史与法制发展的连续性问题
中国法律制度的发展演变具有连续性与阶段性。比方说八议制度,起源于周朝的“八辟”;三国时期魏明帝制定“新律”时,首次写入法典,从此时起至明清。八议制度的发展与朝代的更替没有多大的关联。因此,现行的“断代史”体例并不适合中国法制史自身的发展特点。
“中国法制史虽然历时久远、屡经朝代更替,但自身真正发生质变却只有两次(分别在春秋战国和清末),多数时间特别是在近代以前,一直呈缓慢发展状态,以至于它的许多内容在各朝之间变化细微或固守不前。”[14]
自班固以来,断代为史的方法成为了修史的正宗方法,一姓兴亡成为了历史划分的金标准,理所当然地成为了中国法制史的划分标准。尽管一姓的兴亡与法律的内在发展秩序并不一致。中国当代著名法学家陈顾远(1896-1981)先生认为不应妄依朝代兴亡而求中国法制之变迁。
三、《中国法制史》编撰体例重构设想
在20世纪30年代,陈顾远先生摒弃断代为史的编撰体例,因为妨碍我们认识法制演变的连续性和传统性。陈顾远先生主张“问题研究法”,把中国法制史的变迁分为“创始期”(殷商至战国),“发达期”(秦至南北朝),“确定期”(隋至清),“变革期”(清末至民国)等四个时期。他认为,这种划分更加有助于我们宏观把握数千年中国法制变化的轨迹。[15]
朱勇将中国法制分为形成期、发展期、发达期和近代化时期。
范忠信把中国法制史[16]分为起源时期、争鸣时期、整合时期、定型时期以及变革时期五个时代。“具体言之,起源时期是指远古到西周,争鸣时期主要是指春秋战国,整合时期指秦汉到唐初,把中唐以后到清代中后期称为定型时期,清末变法以后今则称为变革时期。”[17]
邓建鹏也打破了以朝代为标准的划分方式,而以法典自身发展演变的特征划分其时期,即分为:法制初创期、法制公开化时期、法制儒家化时期、法典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