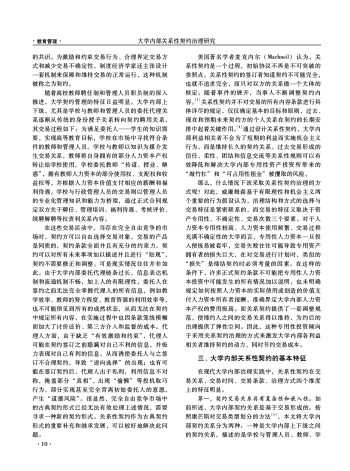随着高校教师聘任制和管理人员职员制的深入推进,大学契约管理的特征日益明显。大学内部上下级,尤其是学校与教师和管理人员的委托代理关系逐渐从传统的身份授予关系转向契约聘用关系,其交易过程如下:为满足委托人——学生的知识需要,实现高等教育目标,学校在市场中寻找符合条件的教师和管理人员。学校与教师以知识为媒介发生交易关系,教师将自身拥有的部分人力资本产权转让给学校使用,学校委托教师“传道、授业、解惑”,拥有教师人力资本的部分使用权、支配权和收益权等,并根据人力资本价值支付相应的薪酬和福利待遇。学校与行政管理人员的交易则以管理人员的专业化管理知识和能力为桥梁,通过正式合同规定双方关于聘任、管理培训、福利待遇、考核评价、续聘解聘等权责利关系内容。
在这些交易活动中,当存在完全自由竞争的市场时,契约方可以自由选择交易对象,交易的产品是同质的,契约条款全面并且有充分的约束力。契约可以对所有未来事项加以描述并且进行“贴现”,契约不需要修正和调整。可是现实情况往往并非如此。由于大学内部委托代理链条过长,信息表达机制和流通机制不畅,加上人的有限理性,委托人在签约之前无法完全掌握代理人的所有信息,例如教学效率、教师的努力程度、教育资源的利用效率等,也不可能预见到所有的或然状态,从而无法在契约中规定所有内容,在实施过程中也因条款笼统模糊而加大了讨价还价、第三方介入和监督的成本。代理人方面,由于缺乏“有效激励和约束”,代理人可能在契约签订之前隐瞒对自己不利的信息,并极力表现对自己有利的信息,从而诱使委托人与之签订不合理契约,导致“逆向选择”的出现;也有可能在签订契约后,代理人出于私利,利用信息不对称,掩盖部分“真相”, 出现“偷懒”等投机取巧行为,部分实现甚至完全背离初始委托人的意愿,产生“道德风险”。很显然,完全自由竞争市场中的古典契约形式已经无法有效处理上述情况,需要寻求一种新的契约形式。关系性契约作为古典契约形式的重要补充和继承发展,可以较好地解决此问题。
美国著名学者麦克内尔(Machneil)认为,关系性契约是一个过程,初始协议不再是不可突破的参照点。关系性契约的签订者知道契约不可能完全,也就不追求完全,而只对双方的关系做一个大体的框定。随着事件的展开,当事人不断调整契约内容。[3]关系性契约并不对交易的所有内容条款进行具体详尽的规定,仅仅确定基本的目标和原则,过去、现在和预期未来契约方的个人关系在契约的长期安排中起着关键作用。[4]通过设计关系性契约,大学内部利益相关者不会为了短期的利益而实施机会主义行为,而是维持长久的契约关系。过去交易形成的信任、柔性、团结和信息交流等关系性规则可以有效降低和解决大学内部专用性资产投资所带来的“敲竹杠”和“可占用性租金”被攫取的风险。
那么,什么情况下该采取关系性契约治理的方式呢?对此,威廉姆森基于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两个重要的行为假设认为,治理结构和方式的选择与交易特征是紧密联系的,而交易的特征又取决于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交易次数三个要素。对于人力资本专用性较高、人力资本使用频繁、交易过程充满不确定性的大学而言,专用性人力资本一旦投入便极易被套牢,交易失败往往可能导致专用资产拥有者的损失巨大,在对交易进行计划时,类似的“损失”是缔结契约时必须考量的因素。在这样的条件下,许多正式契约条款不可能把专用性人力资本投资中可能发生的所有情况加以说明,也未明确规定如何按照人力资本的实际使用或创造的价值支付人力资本所有者报酬,准确界定大学内部人力资本产权的费用极高。而关系契约提供了一套调整规范,使缔约人之间的交易关系得以维持,为约后的治理提供了弹性空间。因此,这种专用性投资倾向于采用关系契约治理的方式来激发大学内部各利益相关者维持契约的动力,同时节约交易成本。
三、 大学内部关系性契约的基本特征
在现代大学内部治理实践中,关系性契约在交易关系、交易时间、交易条款、治理方式四个维度上的特征明显。
第一,契约交易关系具有复杂性和嵌入性。如前所述,大学内部契约关系是基于交易形成的。按照康芒斯对交易类型划分的方法[5],本文将大学内部契约关系分为两种:一种是大学内部上下级之间的契约关系,描述的是学校与管理人员、教师、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