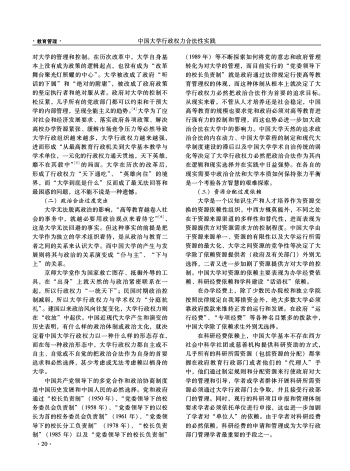(二)政治合法过度突出
大学无法脱离政治的影响,“高等教育越卷入社会的事务中,就越必要用政治观点来看待它”[6],这是大学无法回避的事实。但这种事实的前提是把大学作为独立的学术组织看待,是从政治与教育二者之间的关系来认识大学。而中国大学的产生与发展则将其与政治的关系演变成“仆与主”、“下与上”的关系。
京师大学堂作为国家救亡图存、抵御外辱的工具,在“出身”上就天然的与政治紧密联系在一起,所以行政权力“一统天下”;民国时期政治控制减弱,所以大学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分庭抗礼”。建国以来政治风向往复变化,大学行政权力则在“收放”中起伏。中国近现代大学产生和演变的历史表明,有什么样的政治体制或政治文化,就决定着中国大学行政权力以一种什么样的形态存在,而在每一种政治形态中,大学行政权力都自主或不自主、自觉或不自觉的把政治合法作为自身的首要追求和必然选择,甚少考虑或无法考虑赖以栖身的大学。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历史发展和中国人民的必然选择。党和政府通过“校长负责制”(1950年)、“党委领导下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1958年)、“党委领导下的以校长为首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1961年)、“党委领导下的校长分工负责制”(1978年)、“校长负责制”(1985年)以及“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1989年)等不断探索如何将党的意志和政府管理转化为对大学的管理,而目前实行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就是政府通过法律规定行使高等教育管理权的体现,而这种体制从根本上就决定了大学行政权力必然把政治合法作为首要的追求目标。从现实来看,不管从人才培养还是社会稳定,中国高等教育的规模也要求党和政府必须对高等教育进行强有力的控制和管理,而这也势必进一步加大政治合法在大学中的影响力。中国大学天然的追求政治合法的内在动力、中国大学章程的制定和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滞后以及中国大学学术自治传统的弱化等决定了大学行政权力必然把政治合法作为其内在逻辑和现实选择并在实践中日益强势。在各自的现实需要中政治合法和大学本质如何保持张力平衡是一个考验各方智慧的艰难探索。
(三)资源分配过度依赖
大学是一个以知识生产和人才培养作为资源交换的资源依赖性组织,中西方概莫能外,不同之处在于资源来源渠道的多样性和替代性,进而表现为资源提供方对资源需求方的控制程度。中国大学由于资源来源单一、资源的有限性以及大学运行所需资源的最大化、大学之间资源的竞争性等决定了大学除了依赖资源提供者(政府及有关部门)外别无选择,二者又进一步加剧了资源提供方对大学的控制。中国大学对资源的依赖主要表现为办学经费依赖、科研经费依赖和学科建设“话语权”依赖。
在办学经费上,除了少数民办院校和独立学院按照法律规定自我筹措资金外,绝大多数大学必须靠政府拨款来维持正常的运行和发展。在政府“运行经费”、“专项经费”等各种名目繁多的拨款中,中国大学除了依赖求生外别无选择。
在科研经费依赖上,中国大学基本不存在西方社会中科学社团或慈善机构提供科研资助的方式,几乎所有的科研所需资源(包括资源的分配)都掌握在政府教育行政部门或者他们的“代理人”手中,他们通过制定规则和分配资源来行使政府对大学的管理和引导,学者或学者群体开展科研所需资源必须通过大学行政部门去争取,并且接受行政部门的管理。同时,现行的科研项目申报和管理体制要求学者必须依托单位进行申报,这也进一步加剧了学者对“单位人”的依赖。由于学者对科研经费的必然依赖,科研经费的申请和管理成为大学行政部门管理学者最重要的手段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