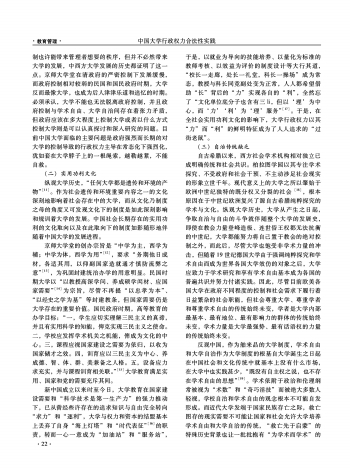(二)实用功利文化
纵观大学历史,“任何大学都是遗传和环境的产物”[11]。作为社会遗传和环境重要内容之一的文化深刻地影响着社会存在中的大学,而从文化乃制度之母的角度又可发现文化下的制度是如此深刻影响和规训着大学的发展。中国社会长期存在的实用功利的文化取向以及在此取向下的制度如影随形地伴随着中国大学的发展进程。
京师大学堂的创办宗旨是 “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12],要求“务期他日成材,各适其用,以仰副国家造就通才慎防流弊之意”[13],为巩固封建统治办学的用意明显。民国时期大学以“以教授高深学问、养成硕学闳材、应国家需要”[14]为宗旨,尽管不再提“以忠孝为本”、“以经史之学为基”等封建教条,但国家需要仍是大学存在的重要价值。国民政府时期,高等教育的办学目标:“一,学生应切实理解三民主义的真谛,并且有实用科学的知能,俾克实现三民主义之使命。二,学校应发挥学术机关之机能,俾成为文化的中心。三,课程应视国家建设之需要为依归,以收为国家储才之效。四,训育应以三民主义为中心、养成德、智、体、群、美兼备之人格。五,设备应力求充实,并与课程训育相关联。”[15]大学教育满足实用、国家和党的需要充斥其间。
新中国成立以来时至今日,大学教育在国家建设需要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强力推动下,已从曾经些许存在的追求知识与自由完全转向“求力”和“逐利”,大学与权力和资本的结盟基本上丢弃了自身“海上灯塔”和“时代表征”[16]的职责,转而一心一意成为“加油站”和“服务站”,于是,以就业为导向的技能培养、以量化为标准的教师考核、以效益为评价的制度设计等大行其道,“校长一走廊,处长一礼堂,科长一操场”成为常态,教授与科长同竞副处变为正常,人人都希望借助“长”背后的“力”实现各自的“利”,全然忘了“文化单位底分子也含有三li,但以‘理’为中心,而‘力’‘利’为‘理’服务”[17]。于是,在全社会实用功利文化的影响下,大学行政权力以其“力”而“利”的鲜明特征成为了人人追求的“过街老鼠”。
(三)自治传统缺乏
自古希腊以来,西方社会学术机构相对独立已成明确传统和社会共识。柏拉图学园以其专注学术探究、不受政府和社会干预、不主动涉足社会现实的形象立世千年。现代意义上的大学之所以肇始于欧洲中世纪独特的既分权又分裂的社会 [18],根本原因在于中世纪欧洲复兴了源自古希腊纯粹探究的学术与文化。纵观大学历史,大学从产生之日起,争取自治与自由的斗争就伴随整个大学的发展史,即使在教会力量登峰造极、连世俗王权都无法抗衡的中世纪,大学都能努力将自己置于教会的绝对控制之外,而此后,尽管大学也饱受非学术力量的冲击,但随着19世纪德国大学由于强调纯粹探究和学术自由而成为世界各国大学效仿的对象之后,大学应致力于学术研究和享有学术自由基本成为各国的普遍共识并努力付诸实践。因此,尽管目前欧美各国大学在政府不同程度的控制和社会需求下履行着日益繁杂的社会职能,但社会尊重大学、尊重学者和尊重学术自由的传统始终未变,学者是大学内部最基本、最有地位、最有影响力的群体的传统始终未变,学术力量是大学最强势、最有话语权的力量的传统始终未变。
反观中国,作为舶来品的大学制度,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作为大学制度的根基自大学诞生之日起在中国社会和文化传统中就基本上没有什么市场,在大学中也实践甚少,“既没有自主权之说,也不存在学术自由的思想”[19]。学术依附于政治和伦理纲常被视为“术数”和“奇巧淫技”而被绝大多数人轻视,学校自治和学术自由的观念根本不可能自发形成。而近代大学发端于国家民族存亡之际,救亡图存的现实需要不可能让国家和社会允许大学培养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的传统,“救亡先于启蒙”的特殊历史背景也让一批批抱有“为学术而学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