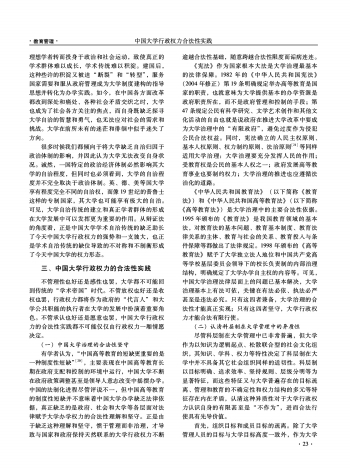很多时候我们都倾向于将大学缺乏自治归因于政治体制的影响,并因此认为大学无法改变自身状况。诚然,一国特定的政治经济体制必然影响其大学的自治程度,但同时也必须看到,大学的自治程度并不完全取决于政治体制。英、德、美等国大学享有程度完全不同的自治权,而像19世纪的普鲁士这样的专制国家,其大学也可能享有极大的自治。可见,大学自治传统的建立和真正学者群体的形成在大学发展中可以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从辩证法的角度看,正是中国大学学术自治传统的缺乏助长了今天中国大学行政权力的强势和一支独大,也正是学术自治传统的缺位导致的不对称和不制衡形成了今天中国大学的权力形态。
三、中国大学行政权力的合法性实践
不管理性也好还是感性也罢,大学都不可能回到传统的“学术帝国”时代。不管放权也好还是收权也罢,行政权力都将作为政府的“代言人”和大学公共职能的执行者在大学的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不管承认也好还是愿意也罢,中国大学行政权力的合法性实践都不可能仅仅由行政权力一厢情愿决定。
(一)中国大学治理的合法性坚守
有学者认为,“中国高等教育的短缺更重要的是一种制度性短缺”[20],主要表现在中国高等教育长期在政府支配和控制的环境中运行,中国大学不断在政府政策调整甚至是领导人意志改变中摇摆办学。中国的法制化进程尽管评说不一,但中国高等教育的制度性短缺并不意味着中国大学办学缺乏法律依据,真正缺乏的是政府、社会和大学等各层面对法律赋予大学办学权力的合法性理解和坚守。正是由于缺乏这种理解和坚守,惯于管理而非治理,才导致与国家和政府保持天然联系的大学行政权力不断逾越合法性基础,随意跨越合法性限度而诟病连连。
《宪法》作为国家根本大法是大学治理最基本的法律保障。1982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2004年修正)第19条明确规定举办高等教育是国家的职责,也就意味为大学提供基本的办学资源是政府职责所在,而不是政府管理和控制的手段;第47条规定公民有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也就是说政府在推进大学改革中要成为大学治理中的“有限政府”,避免过度作为侵犯公民合法权益。同时,宪法确立的人民主权原则、基本人权原则、权力制约原则、法治原则[21]等同样适用大学治理:大学治理要充分发挥人民的作用;受教育权是公民的基本人权之一;政府发展高等教育事业也要制约权力;大学治理的推进也应遵循法治化的道路。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以下简称《教育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以下简称《高等教育法》)是大学治理中的主要合法性依据。1995年颁布的《教育法》是我国教育领域的基本法,对教育法的基本问题、教育基本制度、教育法律关系的主体、教育与社会的关系、教育投入与条件保障等都做出了法律规定。1998年颁布的《高等教育法》赋予了大学独立法人地位和中国共产党高等学校基层委员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的内部治理结构,明确规定了大学办学自主权的内容等。可见,中国大学治理法律层面上的问题已基本解决,大学治理基本上有法可依,关键在有法必依、执法必严甚至是违法必究。只有这四者兼备,大学治理的合法性才能真正实现;只有这四者坚守,大学行政权力才能合法有限行使。
(二)认清科层制在大学管理中的异质性
尽管科层制在大学管理中已非常普遍,但大学作为以知识为逻辑起点、松散联合型的社会文化组织,其知识、学科、权力等特性决定了科层制在大学中并不具备其它社会组织同样的适切性。科层制以目标明确、追求效率、坚持规则、层级分明等为显著特征,而这些特征又与大学普遍存在的目标疏离、管理和教育的不确定性和权力结构的多元等特征存在内在矛盾,认清这种异质性对于大学行政权力认识自身的有限甚至是“不作为”,进而合法行使具有先导价值。
首先,组织目标和成员目标的疏离。除了大学管理人员的目标与大学目标高度一致外,作为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