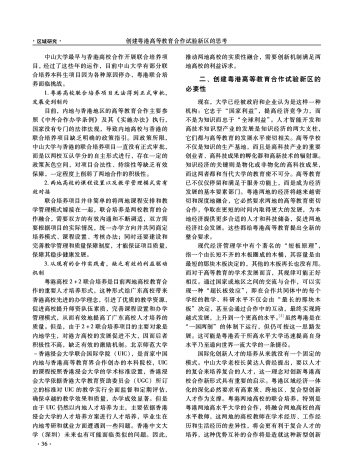1.粤港高校联合培养项目无法得到正式审批,发展受到制约
目前,内地与香港地区的高等教育合作主要参照《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及其《实施办法》执行,国家没有专门的法律法规,导致内地高校与香港的联合培养项目缺乏明确的政策指引。因政策所限,中山大学与香港的联合培养项目一直没有正式审批,而是以两校互认学分的自主形式进行,存在一定的政策灰色空间,对项目合法性、持续性等缺乏有效保障,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两地合作的积极性。
2.两地高校的课程设置以及教学管理模式需有效对接
联合培养项目并非简单的将两地课程安排和教学管理模式嫁接在一起,联合培养是两校教育的合作融合,需要双方的有效沟通和不断调适,双方需要根据项目的实际情况,统一办学方向并共同商定培养模式、课程设置、考核办法;同时还要建设和完善教学管理和质量保障制度,才能保证项目质量,保障其稳步健康发展。
3.从现有的合作实践看,缺乏有效的利益驱动机制
粤港高校2+2联合培养是目前两地高校教育合作的重要人才培养形式,这种形式给广东高校带来香港高校先进的办学理念,引进了优质的教学资源,促进高校提升师资队伍素质,完善课程设置和办学管理模式,从而有效地提高了广东高校人才培养的质量。但是,由于2+2联合培养项目的主要对象是内地学生,对港方高校的发展促进不大,因而后者积极性不高,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UIC),是首家中国内地与香港高等教育界合作创办的本科院校,UIC的课程按照香港浸会大学的学术标准设置,香港浸会大学依据香港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UGC)所订立的标准对UIC的教学实行全面监督和定期评估,确保卓越的教学效果和质量,办学成效显著。但是由于UIC仍然以内地人才培养为主,主要依据香港浸会大学的人才培养方案进行人才培养,毕业生在内地考研和就业方面遭遇到一些问题。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未来也有可能面临类似的问题。因此,推动两地高校的实质性融合,需要创新机制满足两地高校的利益诉求。
二、创建粤港高等教育合作试验新区的必要性现在,大学已经被政府和企业认为是这样一种机构:它忠于“国家利益”,提高经济竞争力,而不是为知识而忠于“全球利益”。人才智能开发和高技术知识型产业的发展是知识经济的两大支柱,它们都与高等教育的发展水平密切相关。高等学校不仅是知识的生产基地,而且是高科技产业的重要创业者、高科技成果的孵化器和高新技术的辐射源。知识经济的关键则是物化或非物化的高科技成果,而这两者都和当代大学的教育密不可分。高等教育已不仅仅停留和满足于服务功能上,而是成为经济发展的基本要素部门。粤港两地的经济将越来越密切和深度地融合,它必然要求两地的高等教育密切合作,争取在更短的时间内取得更大的发展,为本地经济提供更多合适的人才和科技储备,促进两地经济社会发展。这些都给粤港高等教育提出全新的整合要求。
现代经济管理学中有个著名的“短板原理”,指一个由长短不齐的木板圈成的木桶,其容量是由最短的那块木板决定的,其他的木板再长也没有用。而对于高等教育的学术发展而言,其规律可能正好相反。通过国家或地区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可以实现一种“超长板效应”,即在合作共同体中的每个学校的教学、科研水平不仅会由“最长的那块木板”决定,甚至会通过合作中的互动,最终实现跨越式发展,上升到一个更高的水平。[2]虽然粤港是在“一国两制”的体制下运行,但仍可按这一思路发展。这可能是粤港若干所高水平大学迅速提高自身水平乃至通向世界一流大学的一条捷径。
国际化创新人才的培养从来就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中山大学老校长黄达人曾经提出,要以人才的复合来培养复合的人才,这一理念对创新粤港高校合作新形式具有重要的启示。粤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深化必然要求有高素质、跨地区、复合型创新人才作为支撑。粤港两地高校的联合培养,特别是粤港两地高水平大学的合作,将融合两地高校的高水平教师,这两地的高校教师在学术经历、工作经历和生活经历的差异性,将会更有利于复合人才的培养,这种优势互补的合作将是造就这种新型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