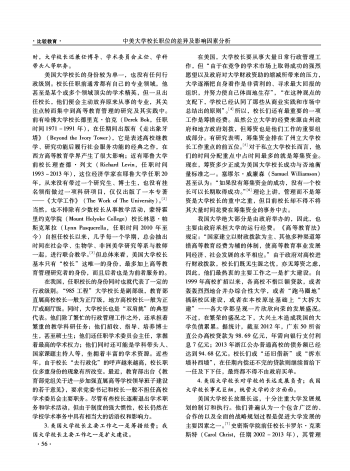美国大学校长的身份较为单一,也没有任何行政级别。校长任职前通常都有自己的专业领域,他甚至是某个或多个领域顶尖的学术精英,但一旦出任校长,他们便会主动放弃原来从事的专业,其关注点转而集中到高等教育管理的研究及其实践中。前有哈佛大学校长德里克·伯克(Derek Bok,任职时间1971-1991年),在任期间出版有《走出象牙塔》(Beyond the Ivory Tower),它是表述高校继教学、研究功能后履行社会服务功能的经典之作,在西方高等教育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近有耶鲁大学前校长理查德·列文(Richard Levin,任职时间1993-2013年),这位经济学家在耶鲁大学任职20 年,从来没有带过一个研究生、博士生,也没有挂名领衔做过一项科研项目,仅仅出版了一本专著——《大学工作》(The Work of The University)。[2]当然,也不排除有少数校长从事教学活动,蒙特霍里约克学院(Mount Holyoke College)校长林恩·帕斯克莱拉(Lynn Pasquerella,任职时间2010年至今)自担任校长以来,几乎每一个学期,总会抽出时间在社会学、生物学、非洲美学研究等系与教师一起,进行联合教学。[3]但总体来看,美国大学校长基本只有“校长”这唯一的身份,最多加上高等教育管理研究者的身份,而且后者也是为前者服务的。
在我国,任职校长的身份同时也就代表了一定的行政级别。“985工程”大学校长是副部级,教育部直属高校校长一般为正厅级,地方高校校长一般为正厅或副厅级。同时,大学校长也是“双肩挑”的典型代表。他们除了繁忙的行政管理工作之外,还承担着繁重的教学科研任务:他们招收、指导、培养博士生,甚至硕士生;他们还任职学术委员会主任,掌握着最高的学术权力;他们同时还可能是学科带头人、国家课题主持人等,坐拥着丰富的学术资源。近些年,由于校长“去行政化”的呼声越来越高,校长职位多重身份的现象有所改变。最近,教育部出台《教育部党组关于进一步加强直属高等学校领导班子建设的若干意见》,要求党委书记和校长一般不担任高校学术委员会主要职务。尽管有些校长逐渐退出学术职务和学术活动,但由于制度的强大惯性,校长仍然在学校学术事务中具有相当大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3.美国大学校长主要工作之一是筹措经费;我国大学校长主要工作之一是扩大建设。
在美国,大学校长要从事大量日常行政管理工作,但“由于在竞争的学术市场上取得成功的强烈愿望以及政府对大学财政资助的缩减所带来的压力,大学逐渐把自身看作是非营利的、寻求最大回报的组织,并努力使自己体面地生存”,“在这种观点的支配下,学校已经认同了那些从商业实践和市场中总结出的原则”。[4]所以,校长们还有最重要的一项工作是筹措经费。虽然公立大学的经费来源由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划拨,但筹资也是他们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研究表明,筹集资金排在了州立大学校长工作重点的前五位。[5]对于私立大学校长而言,他们的时间分配重点中占时间最多的就是筹集资金。现在,筹资多少正成为美国大学校长成功与否地衡量标准之一。塞缪尔·威廉森(Samuel Williamson)甚至认为:“如果没有筹集资金的成功,没有一个校长可以长期取得成功。”[6]理论上讲,管理而不是筹资是大学校长的重中之重,但目前校长却不得不将其大量时间花费在筹集资金的事务中去。
我国大学绝大部分是由政府举办的,因此,也主要由政府承担大学的运行经费。《高等教育法》规定:“国家建立以财政拨款为主、其他多种渠道筹措高等教育经费为辅的体制,使高等教育事业发展同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相应。”由于政府对高校进行财政拨款,校长们既无生源之忧,亦无筹资之虑,因此,他们最热衷的主要工作之一是扩大建设。自1999年高校扩招以来,各高校不惜巨额贷款,或者轰轰烈烈地合并办综合性大学,或者“跑马圈地”搞新校区建设,或者在本校原址基础上“大拆大建”……各大学都呈现一片欣欣向荣的发展盛况。不过,在繁荣的盛况之下,大兴土木造成我国的大学负债累累。据统计,截至2012年,广东50所省直公办高校贷款为98.69亿元,年需向银行支付利息7亿元;2013年浙江公办普通高校的债务额已经达到94.68亿元。校长们或“还旧借新”或“拆东墙补西墙”,在任期内偿还不完的贷款则继续留给下一任及下下任,最终都不得不由政府买单。
4.美国大学校长对学校的长远发展负责;我国大学校长事无巨细,统管大学的方方面面。
美国大学校长放眼长远,十分注重大学发展规划的制订和执行。他们普遍认为一个包含广泛的、合作的以及全面的战略规划过程是促进大学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7]史密斯学院前任校长卡罗尔·克莱斯特(Carol Christ,任期2002-2013年),其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