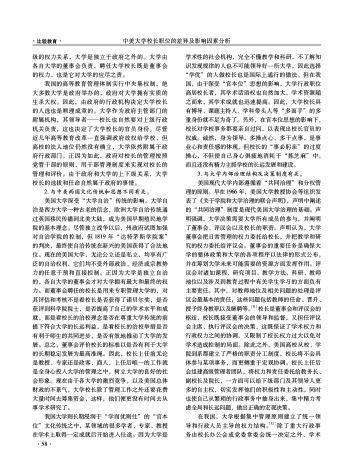我国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实行中央集权制,绝大多数大学是政府举办的,政府对大学拥有实质的生杀大权。因此,由政府的行政机构决定大学校长的人选也是顺理成章的。大学作为政府主管部门的附属机构,其领导者——校长也自然要对上级行政机关负责,这也决定了大学校长的官员身份。尽管近几年高等教育改革一直强调政府放权给学校,但高校的法人地位仍然没有确立,大学依然附属于政府行政部门。正因为如此,政府对校长的管理按照党管干部的原则,用干部管理制度来实现对校长的管理和评价。由于政府和大学的上下级关系,大学校长的选拔和任命自然属于政府的事情。
2.与中美两国文化传统和思想不同有关。
美国大学深受“大学自治”传统的影响。大学自治是西方大学一种古老的信念,欧洲大学自治传统通过英国移民传播到北美大陆,成为美国早期殖民地学院的基本理念。尽管独立战争以后,州政府试图加强对自治学院的控制,但1819年“达特茅斯学院案”的判决,最终使自治传统在新兴的美国获得了合法地位。现在的美国大学,无论公立还是私立,均享有广泛的自治权利,它们均不受外部政治、经济或宗教势力的任意干预和直接控制。正因为大学是独立自治的,各自大学的董事会才对大学拥有最大和最终的权力。而董事会聘任的校长是用来专职管理大学的,对其评估和考核不是看校长是否获得了诺贝尔奖,是否获评到科学院院士,是否提高了自己的学术水平和成就,而是看校长的治校理念是否在尊重大学传统的前提下符合大学的长远利益,是看校长的治校举措是否有利于师生的共同进步,是否有效地推动了大学的发展。总之,董事会评价校长的标准以是否有利于大学的长期稳定发展为最高准绳。因此,校长上任前无论是教授、专家还是政客、商人,上任后唯一的工作就是全身心投入大学的管理之中,树立大学的良好的社会形象。现在由于各大学的激烈竞争,以及美国总体财政的不景气,大学校长除了管理工作之外还要花费大量时间去筹集资金,这样,他们便更没有时间去从事学术研究了。
我国大学则长期浸润于“学而优则仕”的“官本位”文化传统之中,某领域的很多学者、专家、教授在学术上取得一定成就后开始进入仕途。因为大学是学术性的社会机构,完全不懂教学和科研,不了解知识发现规律的人也不可能领导好一所大学,因此选择“学优”的人做校长也是国际上通行的做法。但在我国,由于深受“官本位”思想的影响,大学行政职位高居校长者,其学术话语权也自然加大,学术资源随之而来,其学术成就也迅速提高。因此,大学校长具有博导、课题主持人、学科带头人等“多面手”的多重身份就不足为奇了。另外,在官本位思想的影响下,校长对学校事务都要亲自过问,以表现出校长官员的权威。诚然,身为领导,多操点心、多干点事,是事业心和责任感的体现,但校长的“事必躬亲”的过度操心,不但使自己身心俱疲地消耗于“拣芝麻”中,而且还没有精力主抓学校的长远发展和建设。
3.与大学内部治理结构及决策制度有关。
美国现代大学内部遵循着“共同治理”和分权管理的原则。早在1966年,美国大学教授协会等组织发表了《关于学院和大学治理的联合声明》,声明中阐述的“共同治理”制度是现代美国大学治理的基础。声明强调,大学决策需要大学所有成员的参与,并阐明了董事会、评议会以及校长的职责。声明认为,大学董事会把日常管理的权力委托给校长,并把教学和研究的权力委托给评议会。董事会的重要任务是确保大学的整体政策和大学的各项程序以法律的形式公布,并在筹划大学未来可能需要的资源方面发挥作用。评议会对诸如课程、研究项目、教学方法、科研、教师地位以及涉及到教育过程中有关学生学习的方面负有主要责任。其中,对教师地位及相关问题的处理是评议会最基本的责任,这些问题包括教师的任命、晋升、授予终身教职以及解聘等。[11]校长是董事会和评议会的枢纽,校长既接受董事会的领导和监督,又担任评议会主席、执行评议会的决策,这既保证了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之间的协调,又限制了校长权力过大以免对学术造成控制的局面。除此之外,美国高校从校、学院到系都建立了严格的职责分工制度,校长将不会具体参与某项事务,而更侧重于宏观协调。校长上任后会组建高级管理者团队,将权力和责任委托给教务长、副校长及院长,一方面可以给下级部门及其领导人更多的自主权,切实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同时也使自己从繁琐的行政事务中抽身出来,集中精力考虑全局和长远问题,做出正确的宏观决策。
在我国,大学根据集中管理原则建立了统一领导和行政人员主导的权力结构。[12]除了重大行政事务由校长办公会或党委常委会统一决定之外,学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