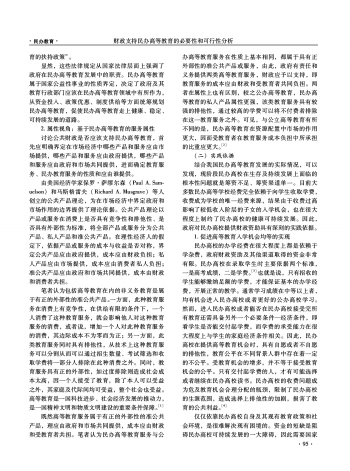显然,这些法律规定从国家法律层面上强调了政府在民办高等教育发展中的职责。民办高等教育属于国家公益性事业的性质界定,决定了政府及其教育行政部门应该在民办高等教育领域中有所作为,从资金投入、政策优惠、制度供给等方面统筹规划民办高等教育,促使民办高等教育走上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2.属性视角:基于民办高等教育的服务属性
讨论公共财政是否应该支持民办高等教育,首先应明确界定在市场经济中哪些产品和服务应由市场提供,哪些产品和服务应由政府提供,哪些产品和服务应由政府和市场共同提供,进而确定教育服务、民办教育服务的性质和应由谁提供。
由美国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Paul A.Samuelson)和马斯格雷夫(Richard A.Musgrave)等人创立的公共产品理论,为在市场经济中界定政府和市场作用的边界提供了理论依据。公共产品理论以产品或服务在消费上是否具有竞争性和排他性、是否具有外部性为标准,将全部产品或服务分为公共产品、私人产品和准公共产品。在理性经济人的假定下,依据产品或服务的成本与收益是否对称,界定公共产品应由政府提供,成本应由财政负担;私人产品应由市场提供,成本应由消费者私人负担;准公共产品应由政府和市场共同提供,成本由财政和消费者共担。
笔者认为包括高等教育在内的非义务教育是属于有正的外部性的准公共产品。一方面,此种教育服务在消费上有竞争性,在供给有限的条件下,一个人消费了这种教育服务,就会影响他人对这种教育服务的消费,或者说,增加一个人对此种教育服务的消费,其边际成本不为零而为正;另一方面,此类教育服务同时具有排他性,从技术上这种教育服务可以分割从而可以通过招生数量、考试筛选和收取学费将一部分人排除在此种消费之外。同时,教育服务具有正的外部性,如过度排除则造成社会成本太高,因一个人接受了教育,除了本人可以受益之外,其家庭及代际间均可受益,整个社会也受益。高等教育是一国科技进步、社会经济发展的推动力,是一国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的重要条件保障。[1]
既然高等教育服务属于有正的外部性的准公共产品,理应由政府和市场共同提供,成本应由财政和受教育者共担。笔者认为民办高等教育服务与公办高等教育服务在性质上基本相同,都属于具有正外部性的准公共产品或服务,由此,政府有责任和义务提供两类高等教育服务,财政应予以支持,即教育服务的成本应由财政和受教育者共同负担。两者在属性上也有区别,较之公办高等教育,民办高等教育的私人产品属性更强,该类教育服务具有较强的排他性,通过较高的学费可以将不付费者排除在这一教育服务之外。可见,与公立高等教育有所不同的是,民办高等教育在资源配置中市场的作用更大,因而受教育者在教育服务成本负担中所承担的比重应更大。[2]
(二)实践依据
结合我国民办高等教育发展的实际情况,可以发现,现阶段民办高校在生存及持续发展上面临的根本性问题就是筹资不足、筹资渠道单一。目前大多数民办高等学校经费完全依赖于向学生收取学费,收费成为学校的唯一经费来源,结果由于收费过高影响了较低收入阶层的子女的入学机会,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民办高校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因此,政府对民办高校提供财政资助具有深刻的实践依据。
1.促进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均等的实现
民办高校的办学经费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依赖于学杂费,政府财政资助及其他渠道取得的资金非常有限。民办高校在录取学生时主要依据两个标准,一是高考成绩,二是学费。[3]也就是说,只有招收的学生能够缴纳足额的学费,才能保证基本的办学经费,开展正常的教学。通常学习成绩在中等以上者,均有机会进入民办高校或者更好的公办高校学习。然而,进入民办高校或者能否在民办高校接受完所有教育还需具备另外一个必要条件—经济条件,即看学生是否能交付起学费,而学费的承受能力在很大程度上与学生的家庭经济条件相关。因此,民办高校在提供高等教育机会时,具有自愿或者不自愿的排他性,教育公平在不同背景人群中存在着一定的不公平。受教育机会的增多,并不等于接受教育机会的公平。只有交付起学费的人,才有可能选择或者继续在民办高校读书。民办高校的收费问题成为危及教育机会合理分配的瓶颈,限制了民办高校的生源范围,造成选择上排他性的加剧,损害了教育的公共利益。[4]
仅仅依靠民办高校自身及其现有教育政策和社会环境,是很难解决现有困境的。资金的短缺是阻碍民办高校可持续发展的一大障碍,因此需要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