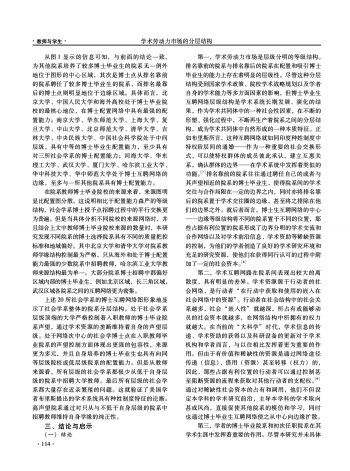从图1显示的信息可知,与前面的结论一致,为其他院系培养了较多博士毕业生的院系无一例外地位于图形的中心区域,其次是博士点从排名靠前的院系聘任了较多博士毕业生的院系,而排名最靠后的博士点则明显地位于边缘区域。具体而言,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海外高校处于博士毕业院校的最核心地位,在博士配置网络中具有最强的配置能力;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吉林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处于中间层级,具有中等的博士毕业生配置能力,至少具有对三所社会学系的博士配置能力;河海大学、华东理工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处于博士互聘网络的边缘,至多与一所其他院系具有博士配置能力。
在院系教师博士毕业院校的来源来看,来源图明显比配置图分散,这说明相比于配置能力森严的等级结构,社会学系博士授予点招聘过程中的平行交换更为普遍。但是当具体分析不同院校的来源网络时,并且结合上文中教师博士毕业院校来源的数量时,本研究发现不同院系的博士选择院系具有不同的质量把控标准和地域偏好。其中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对院系教师学缘结构控制最为严格,只从海外和处于博士配置能力最强的少数院系中招聘教师,哈尔滨工业大学教师来源结构最为单一。大部分院系博士招聘中都偏好区域内部的博士毕业生,例如北京区域,长三角区域,武汉区域各院系之间的互聘网络更为密集。
上述20所社会学系的博士互聘网络图形象地显示了社会学系整体的院系分层结构。处于社会学系层级顶端的大学严格控制着入职教师的博士毕业院系声望,通过学术资源的垄断维持着自身的声望层级。处于网络次中心的社会学博士点在入职教师毕业院系的声望控制方面体现出更强的包容性,来源更为多元,并且自身培养的博士毕业生也具有向同等层级院校或低层级院系的配置能力。但是从教师来源看,所有层级的社会学系都极少从低于自身层级的院系中招聘大学教师。最后所有层级的社会学系都大量存在近亲繁殖的问题。这就验证了美国学者布里斯提出的学术系统具有种姓制度特征的论断。高声望院系通过对只从与不低于自身层级的院系中招聘教师维持自身学缘的纯正性。
三、结论与启示
(一)结论
第一,学术劳动力市场是层级分明的等级结构。排名靠前的院系与排名靠后的院系在配置和吸引博士毕业生的能力上存在着明显的层级性。尽管这种分层结构受到国家学术政策、院校学术战略规划以及学者自身的学术能力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但博士毕业生互聘网络层级结构是学术系统长期发展、演化的结果,作为学术共同体中的一种社会性因素,在不断的形塑、强化过程中,不断再生产着院系之间的分层结构,成为学术共同体中自然形成的一种本质特征。正如布里斯所言,这种互聘网络就如同印度种姓制度中特权阶层间的通婚———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交换形式,可以使特权群体的成员彼此承认,建立互惠关系,确认群体的边界———在学术系统中发挥着类似的功能。排名靠前的院系往往通过聘任自己的或者与其声望相近的院系的博士毕业生,使得院系间的学术交往与合作局限在一定的边界之内,同时亦将排名靠后的院系置于学术交往圈的边缘,甚至将之排除在他们的边界之外。就后者而言,博士生互聘网络的中心———边缘等级结构将不同的院系置于不同的位置,那些占据有利位置的院系形成了边界分明的学术交流和合作网络以及对学术前沿信息、学术资助等稀缺资源的控制,为他们的学者创造了良好的学术研究环境和充足的研究资源,使他们在获得同行认可的过程中附加了一定的社会资本。
第二,学术互聘网路在院系间表现出较大的离散度,具有明显的差异。学术资源源于行动者的社会网络,是行动者“在行动中获取和使用的嵌入在社会网络中的资源”。行动者在社会结构中的社会关系越多,社会“嵌入性”就越深,所占有或能够动员的社会资本就越多,在网络结构中所拥有的权力就越大。在当前的“大科学”时代,学术信息的传递、学术资助的获得以及科研设备的更新对于学术机构和学者而言,与以往相比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但由于有价值和稀缺性的资源是通过网络途径传递(信息)、借用(资源)甚至转移(权力)的,因此,那些占据有利位置的行动者可以通过控制甚至阻断资源的流程来获取对其他行动者的支配权。通过对稀缺性社会资本的占有和调用,他们不但设定本学科的学术研究前沿,主导本学科的学术取向甚或风尚,直接促使其他院系的模仿和学习,同时也通过博士毕业生互聘网络使之从中心向边缘扩散。
第三,学者的博士毕业院系和初次任职院系在其学术生涯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尽管本研究并未具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