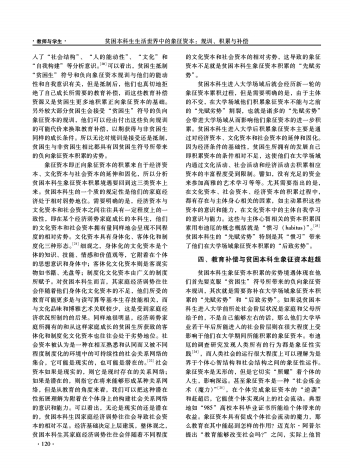入了“社会结构”、“人的能动性”、“文化”和“自我构建”等分析意识。 可以看出,贫困生抵制“贫困生”符号和负向象征资本规训与他们的能动性和自我意识有关,但是抵制后,他们也真切地拒绝了自己成长所需要的教育补偿,而这些教育补偿资源又是贫困生更多地积累正向象征资本的基础。另外较大部分贫困生会接受“贫困生”符号的负向象征资本的规训,他们可以经由付出这些负向规训的可能代价来换取教育补偿,以期获得与非贫困生同样的成长条件。所以无论对规训是接受还是抵制,贫困生与非贫困生相比都具有因贫困生符号所带来的负向象征资本积累的劣势。
象征资本即正向象征资本的积累来自于经济资本、文化资本与社会资本的延伸和固化,所以分析贫困本科生象征资本积累境遇要回到这三类资本上来。贫困本科生的一个质的规定性是他们的家庭经济处于相对弱势地位。需要明确的是,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之间往往具有一定程度上的一致性,即在某个经济弱势家庭成长的本科生,他们的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拥有量同样地会呈现不同程度的相对劣势。文化资本具有身体化、客体化和制度化三种形态。 细观之,身体化的文化资本是个体的知识、技能、情感和价值观等,它附着在个体的思想意识和身体中;客体化文化资本则是客观实物如书籍、光盘等;制度化文化资本由广义的制度所赋予。对贫困本科生而言,其家庭经济弱势往往会伴随着他们身体化文化资本的不足,他们所受的教育可能更多是与读写算等基本生存技能相关,而与文化品味和博雅艺术关联较少,这是受到家庭经济状况所制约的后果。同样地很明显,经济弱势家庭所拥有的和从这样家庭成长的贫困生所获致的客体化和制度化文化资本也往往会处于劣势地位。社会资本被认为是一种在相互熟悉和认同而又被不同程度制度化的环境中的可持续性的社会关系网络的集合,它可能是现实的,也可能是潜在的。 社会资本如果是现实的,则它是现时存在的关系网络;如果是潜在的,则指它在将来能够形成某种关系网络,但是从教育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把这种潜在性拓展理解为附着在个体身上的构建社会关系网络的意识和能力。可以看出,无论是现实的还是潜在的,贫困本科生因家庭经济弱势往往会导致社会资本的相对不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整体观之,贫困本科生其家庭经济弱势往往会伴随着不同程度的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的相对劣势,这导致的象征资本不足就是贫困本科生象征资本积累的“先赋劣势”。
贫困本科生进入大学场域后就会经历新一轮的象征资本累积过程,但是需要明确的是,由于主体的不变,在大学场域他们积累象征资本不能与之前的“先赋劣势”割裂,也就是诸多的“先赋劣势”会带进大学场域从而影响他们象征资本的进一步积累。贫困本科生进入大学后积累象征资本主要是通过对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延伸和固化。因为经济条件的基础性,贫困生所拥有的发展自己即积累资本的条件相对不足,这使他们在大学场域内通过文化活动、社会活动和经济活动去积累相应资本的丰富程度受到限制。譬如,没有充足的资金来参加高雅的艺术学习等等。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在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经济资本的积累过程中,都有存在与主体身心相关的因素,如主动累积这些资本的意识和能力,在文化资本中的主体自我学习的意识与能力。这些与主体心智相关的资本积累因素用布迪厄的概念概括就是“惯习(habitus)”。贫困本科生的“先赋劣势”特别是其“惯习”带来了他们在大学场域象征资本积累的“后致劣势”。
四、教育补偿与贫困本科生象征资本赶超
贫困本科生象征资本积累的劣势境遇体现在他们首先要克服“贫困生”符号所带来的负向象征资本规训,其次就是需要弥补在大学场域象征资本积累的“先赋劣势”和“后致劣势”。如果说贫困本科生进入大学前所处社会阶层状况是家庭和父母所给予的,不是自己能够左右的话,那么他们大学毕业若干年后所能进入的社会阶层则在很大程度上受影响于他们在大学期间所能积累的象征资本。布迪厄的调查研究发现人类所有的行为都是象征性实践 ,而人类社会的运行很大程度上可以理解为是界于个体心智结构和社会结构之间的象征性运作。象征资本是无形的,但是它切实“照耀”着个体的人生,影响深远。甚至象征资本是一种“社会炼金术(魔力)”,在个体完成象征资本的“逆袭”和赶超后,它能使个体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典型地如“985”高校本科毕业证书所能给个体带来的收益。象征资本具有促成个体社会流动的魔力,那么教育在其中能起到怎样的作用?迈克尔·阿普尔提出“教育能够改变社会吗?”之问,实际上他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