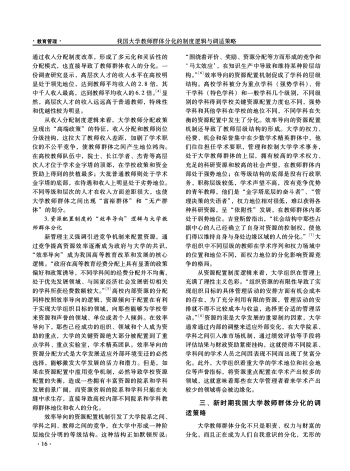通过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形成了多元化和灵活性的分配模式,也直接导致了教师群体收入的分化。一份调查研究显示,高层次人才的收入水平在高校明显处于领先地位,达到教师平均收入的2.8倍,其中千人收入最高,达到教师平均收入的6.2倍。显然,高层次人才的收入远远高于普通教师,特殊性和优越性较为明显。
从收入分配制度逻辑来看,大学教师分配政策呈现出“高端政策”的特征,收入分配和教师岗位分级挂钩,这拉大了教师收入差距,加剧了学术职位的不公平竞争,使教师群体之间产生地位鸿沟。在高校教师队伍中,院士、长江学者、杰青等高层次人才位于学术金字塔的顶部,在学校政策和资金资助上得到的扶植最多;大批普通教师则处于学术金字塔的底部,在待遇和收入上明显处于劣势地位。不同等级和层次的人才在收入方面差距很大,也使大学教师群体之间出现“富裕群体”和“无产群体”的划分。
3.资源配置制度的“效率导向”逻辑与大学教师群体分化
新管理主义强调引进竞争机制来配置资源,通过竞争提高资源效率逐渐成为政府与大学的共识,“效率导向”成为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核心逻辑。“政府在高等教育经费分配上具有显著的政策偏好和政策诱导,不同学科间的经费分配并不均衡,处于优先发展领域、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的学科所获经费数额较大。”高校内部资源的分配同样按照效率导向的逻辑,资源倾向于配置在有利于实现大学组织目标的领域,向那些能够为学校带来资源和声誉的领域、单位或者个人倾斜。在效率导向下,那些己经成功的组织、领域和个人成为资助的重点,大学的关键资源绝大部分被配置到了重点学科、重点实验室,学术精英团队。效率导向的资源分配方式是大学发展适应外部环境变迁的必然选择,能够激发大学发展的活力和潜力。但是,如果在资源配置中滥用竞争机制,必然导致学校资源配置的失衡,造成一些拥有丰富资源的院系和学科发展前景广阔,而资源贫弱的院系和学科只能在夹缝中求生存,直接导致高校内部不同院系和学科教师群体地位和收入的分化。
效率导向的资源配置机制引发了大学院系之间、学科之间、教师之间的竞争,在大学中形成一种阶层地位分明的等级结构。这种结构正如默顿所说:“围绕着评价、奖励、资源分配等方而形成的竞争和‘马太效应’,在知识生产中导致和维持某种阶层结构。”效率导向的资源配置机制促成了学科的层级结构。高校学科被分为重点学科(强势学科)、骨干学科(特色学科)和一般学科几个级别,不同级别的学科得到学校关键资源配置力度也不同,强势学科和其他学科在学校的地位不同,不同学科在失衡的资源配置中发生了分化。效率导向的资源配置机制还导致了教师层级结构的形成。大学的权力、经费、机会和荣誉集中在少数学术精英群体中,他们往往担任学术要职,管理和控制大学学术事务,处于大学教师群体的上层,拥有较高的学术权力、充足的科研资源和较高的社会声望,在教师群体内部处于强势地位;在等级结构的底部是没有行政职务,职称层级较低,学术声望不高,没有竞争优势的青年教师,他们是“金字塔底层的奋斗者”、“管理决策的失语者”,权力地位相对很低,难以获得各种科研资源,呈“依附性”发展,在教师群体内部处于弱势地位。吉登斯曾指出,“社会结构中那些占据中心的人己经确立了自身对资源的控制权,使他们得以维持自身与身处边缘区域的人的分化。” 大学组织中不同层级的教师在学术序列和权力场域中的位置和地位不同,而权力地位的分化影响资源竞争的格局。
从资源配置制度逻辑来看,大学组织在管理上充满了理性主义色彩。“组织资源的有限性导致了实现组织目标的具体管理活动的安排方面有机会成本的存在,为了充分利用有限的资源,管理活动的安排就不得不比较成本与收益,选择更合适的管理活动。”资源约束是大学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大学通常通过内部的调整来适应外部变化,在大学院系、学科之间引入准市场机制,通过绩效评估等手段将评估结果与财政资助紧密挂钩,这就使得不同院系、学科间的学术人员之间因表现不同而出现了贫富分化。此外,大学组织看重大学的学术地位和社会地位等声誉指标,将资源重点配置在学术产出较多的领域,这就意味着那些在大学管理者看来学术产出较少的领域将会被边缘化。
三、新时期我国大学教师群体分化的调适策略
大学教师群体分化不只是职责、权力与财富的分化,而且正在成为人们自我意识的分化,无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