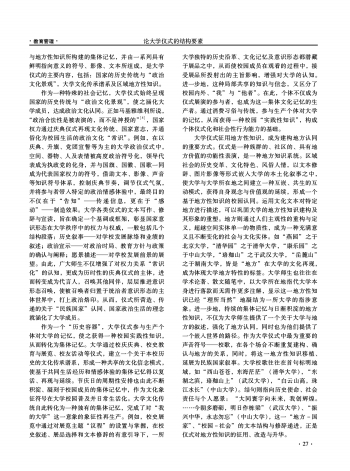与地方性知识所构建的集体记忆,并由一系列具有鲜明指向意义的符号、影像、文本所组成,是大学仪式的主要内容,包括:国家的历史传统与“政治文化景观”,大学文化传承谱系及区域地方性知识。
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记忆,大学仪式始终呈现国家的历史传统与“政治文化景观”,使之涵化大学成员,达成政治文化认同。正如马基雅维利所说,“政治合法性是被表演的,而不是神授的”,国家权力通过庆典仪式再现文化传统、国家意志,并通俗化为校园生活的政治文化“常识”。例如,在以庆典、升旗、党团宣誓等为主的大学政治仪式中,空间、器物、人及表情被高度政治符号化,领导代表成为执政党的化身,并与国旗、国徽、国歌一同成为代表国家权力的符号,借助文本、影像、声音等知识符号体系,控制庆典节奏,调节仪式气氛,并将参与者带入特定的政治情感体验中,最终目的不仅在于“告知”———传递信息,更在于“感动”———制造效果。大学各类仪式的文本写作、修辞与宣读,旨在确定一个基调或框架,彰显国家意识形态在大学秩序中的权力与权威,一般包括几个结构段落:历史叙事———对学校发展脉络和业绩的叙述;政治宣示———对政治时局、教育方针与政策的确认与阐释;愿景描述———对学校发展前景的展望。由此,广大师生不仅增强了对权力关系“常识化”的认知,更成为历时性的庆典仪式的主体,进而转变成为代言人,召唤其他同伴,层层推进意识形态召唤,使被召唤者归置于统治者意识形态的主体世界中,打上政治烙印。从而,仪式所营造、传递的关于“民族国家”认同、国家政治生活的理念就涵化了大学成员。
作为一个“历史容器”,大学仪式参与生产个体对大学的记忆,使之获得一种校园实践性知识,从而转化为集体记忆。大学通过校庆庆典、校史教育与展览、校友活动等仪式,建立一个关于本校历史的文化传承谱系,形成一种共享的文化信念模式,使基于共同生活经历和情感体验的集体记忆得以复活、再现与延续。节庆日的周期性安排也由此不断积淀、凝刻于校园成员的集体记忆中,作为文化象征符号在大学校园普及并日常生活化。大学文化传统自此转化为一种独有的集体记忆,完成了对“我的大学”这一意象的象征性再生产。例如,校史展览中通过对展览主题“议程”的设置与掌握,在校史叙述、展品选择和文本修辞的有意引导下,一所大学独特的历史沿革、文化记忆及意识形态都潜藏于展品之中,从而使校园成员在观看的过程中,接受展品所投射出的主旨影响,增强对大学的认知。进一步地,这种局部共享的知识与信念,又区分了校园内外、“我”与“他者”。在此,个体不仅成为仪式展演的参与者,也成为这一集体文化记忆的生产者。通过消费习俗与传统,参与生产个体对大学的记忆,从而获得一种校园“实践性知识”,构成个体仪式化和社会性行为能力的基础。
大学仪式征用地方性知识,成为建构地方认同的重要方式。仪式是一种族群的、社区的、具有地方价值的功能性表演,是一种地方知识系统。区域社会的历史变革、文化特色、风俗人情,以文本修辞、图片影像等形式嵌入大学的本土化叙事之中,使大学与大学所在地之间建立一种互嵌、共生的互动模式,获得自身观念与价值观的延续,形成一个基于地方性知识的校园认同。运用文化文本对特定地方进行描述,可以巩固大学的地方性知识建构及其形象的重塑。地方则通过人们主观性的重构与定义,超越空间实体单一的物质性,成为一种充满意义且不断变化的社会与文化实体。如“燕园”之于北京大学,“清华园”之于清华大学,“康乐园”之于中山大学,“珞珈山”之于武汉大学,“岳麓山”之于湖南大学,皆是“地方”在大学的文化再现,成为体现大学地方特性的标签。大学师生也往往在学术论著、散文随笔中,以大学所在地指代大学本身进行落款而无需作更多注解,显示这一地方性知识已经“理所当然”地凝结为一所大学的指涉意象。进一步地,持续的集体记忆与日渐积淀的地方性知识,不仅为大学师生提供了一个关于大学与地方的叙述,强化了地方认同,同时也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嵌入世界的路径。作为大学仪式中最为重要的声音符号———校歌,在各个场合不断重复建构、确认与地方的关系,同时,将这一地方性知识移植、延展为民族国家叙事。大学校歌往往在首句标明地域,如“西山苍苍,东海茫茫”(清华大学),“东湖之滨,珞珈山上”(武汉大学),“白云山高,珠江水长”(中山大学)。结句则指向历史使命、社会责任与个人愿景:“大同寰宇向未来,我创辉煌。……今朝多磨砺,明日作栋梁”(武汉大学)、“振兴中华,永志勿忘”(中山大学),这一“地方-国家”、“校园-社会”的文本结构与修辞递进,正是仪式对地方性知识的征用、改造与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