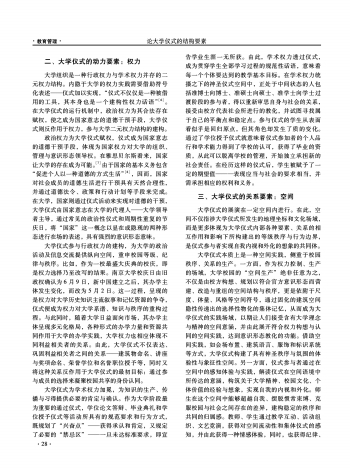二、大学仪式的动力要素:权力
大学组织是一种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并存的二元权力结构。内隐于大学的权力实践需要借助符号化表述——仪式加以实现,“仪式不仅仅是一种被借用的工具,其本身也是一个建构性权力话语”。在大学仪式的运行机制中,政治权力为其合法存在赋权,使之成为国家意志的道德干预手段,大学仪式则反作用于权力,参与大学二元权力结构的建构。
政治权力为大学仪式赋权,仪式成为国家意志的道德干预手段,体现为国家权力对大学的组织、管理与意识形态领导权。在雅思贝尔斯看来,国家让大学的存在成为可能。由于国家的基本义务包含“促进个人以一种道德的方式生活”,因而,国家对社会成员的道德生活进行干预具有天然合理性,并通过道德法令、政策和行动计划等手段来完成。在大学,国家则通过仪式活动来实现对道德的干预,大学仪式由国家意志在大学的代理人——大学领导者主导,通过常见的政治性仪式和周期性重复的节庆日,将“国家”这一概念以显在或隐现的两种形态进行在场的表述,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意味。
大学仪式参与行政权力的建构,为大学的政治活动及信息交流提供纵向空间,重申校园等级、纪律与秩序。比如,作为一校最盛大庆典的校庆,即是权力选择乃至改写的结果。南京大学校庆日由旧政权确认为6月9日,新中国建立之后,其办学主体发生变化,而改为5月2日。这一过程,呈现的是权力对大学历史知识主流叙事和记忆资源的争夺,仪式便成为权力对大学系谱、知识与秩序的重构过程。与此同时,随着大学日益面向市场,其办学主体呈现多元化格局,各种形式的办学力量和资源共同作用于大学的办学实践,大学权力也相应体现不同利益相关者的关系。由此,大学仪式不仅表达、巩固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建筑物命名、讲座与奖项命名、荣誉学位和名誉职位授予等,同时又将这种关系反作用于大学仪式的最初目标:通过参与成员的选择来凝聚校园共享的身份认同。
大学仪式为学术权力加冕,为知识的生产、传播与习得提供必要的肯定与确认。作为大学阶段最为重要的通过仪式,学位论文答辩、毕业典礼和学位授予仪式等活动所具有的规范要求和行为方式,既规划了“兴奋点”——获得承认和肯定,又规定了必要的“禁忌区”—一旦未达标准要求,即宣告学业生涯一无所获。由此,学术权力透过仪式,成为贯穿学生全部学习过程的规范性话语,意味着每一个个体要达到的教学基本目标。在学术权力统摄之下的神圣仪式空间中,正处于中间状态的人包括准博士向博士、准硕士向硕士、准学士向学士过渡阶段的参与者,得以重新审思自身与社会的关系,接受由校方代表社会所进行的教化,并试图寻找属于自己的平衡点和稳定点。参与仪式的学生从表面看似乎是回归原点,但其角色却发生了质的变化。通过了学位授予仪式就意味着仪式参加者的个人品行和学术能力得到了学校的认可,获得了毕业的资质,从此可以脱离学校的管理,开始独立承担新的社会责任。在经历这样的仪式后,学生被赋予了一定的期望值——表现应当与社会的要求相当,并需承担相应的权利和义务。
三、大学仪式的关系要素:空间
大学仪式的展演在一定空间内进行。在此,空间不仅指涉大学仪式所发生的地理坐标和文化场域,而是更多体现为大学仪式内部各种要素、关系的相互作用和影响下所构建出的等级秩序与行为边界,是仪式参与者实现自我内视和外化的想象的共同体。
大学仪式本质上是一种空间实践,侧重于校园秩序、关系的生产。一方面,作为权力控制、生产的场域,大学校园的“空间生产”绝非任意为之,不仅是由校方构想、规划以符合官方意识形态而营建、改造与重组的空间结构与秩序,更是依附于尺度、体量、风格等空间符号,通过固化的建筑空间隐性传递出的选择性物化的集体记忆,从而成为大学仪式的实践场域,以期让人们接受含有大学理念与精神的空间意涵,并由此展开符合权力构想与认同的空间实践,达到意识形态教化的功能。借助空间实践,如会场布置、建筑语言、服饰和标识系统等方式,大学仪式构建了具有神圣秩序与氛围的体验性与象征性空间。另一方面,仪式参与者通过在空间中的感知体验与实践,解读仪式在空间语境中所传达的意涵,构筑关于大学精神、校园文化、个体价值的经验与想象,实现自我的内视和外化。师生在这个空间中能够超越自我、摆脱惯常束缚、克服校园与社会之间存在的差异,建构稳定的秩序和共同的归属感。教师、学生通过教学互动、活动组织、文艺竞演,获得对空间流动性和集体仪式的感知,并由此获得一种情感体验,同时,也获得纪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