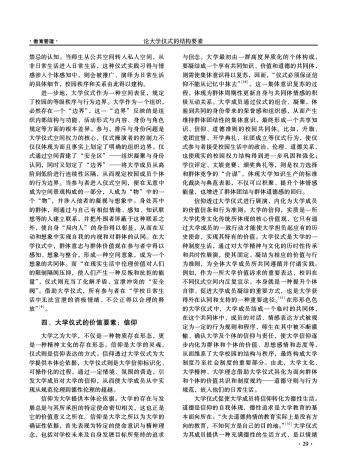禁忌的认知。当师生从公共空间转入私人空间,从非日常生活进入日常生活,这种仪式实践习得与情感涉入个体感知中,则会被推广、演绎为日常生活的具体细节,校园秩序和关系由此得以建构。
进一步地,大学仪式作为一种空间表征,规定了校园的等级秩序与行为边界。大学作为一个组织,必然存在一个“边界”,这一“边界”反映的是组织内部结构与功能、活动形式与内容、身份与角色规定等方面的根本差异。参与、排斥与身份问题是大学仪式空间权力的核心,仪式操演者的控制力不仅仅体现为而且事实上划定了明确的组织边界。仪式通过空间营建了“安全区”———组织凝聚与身份认同,同时又划定了“边界”———将大学成员从高阶到低阶进行连续性区隔,从而规定校园成员个体的行为边界。当参与者进入仪式空间,便在无意中成为空间景观构成的一部分,人成为“物”中的一个“物”,并涉入他者的凝视与想象中。身处其中的群体,则通过与自己有相似情绪、感知、知识联想等的人建立联系,并把外围者屏蔽于这种联系之外,使自身“局内人”的身份得以彰显,从而在互动和想象中实现自我的内视和对群体的认同。在大学仪式中,群体意志与群体价值观在参与者中得以感知、想象与整合,形成一种空间意象,成为一个想象的共同体。而“在现实生活中伦理价值对人们的限制隔阂压抑,使人们产生一种反叛和抗拒的能量”,仪式则充当了化解矛盾、宣泄冲突的“安全阀”。借助大学仪式,所有参与者在“学校日常生活中无法宣泄的消极情绪、不公正得以合理的释放”。
四、大学仪式的价值要素:信仰
大学之为大学,不仅是一种物质存在形态,更是一种精神文化的存在形态。信仰是大学的灵魂,仪式则是信仰表达的方式。信仰透过大学仪式为大学提供本体论依据,大学仪式则是大学信仰标识化、可操作化的过程,通过一定情境、氛围的营造,引发大学成员对大学的信仰,从而使大学成员从中实现从规范伦理到德性伦理的超越。
信仰为大学提供本体论依据。大学的存在与发展总是与其所承担的特定使命密切相关,这也正是它的价值意义之所在。信仰是大学之所以为大学的确证性依据,首先表现为特定的使命意识与精神理念,包括对学校未来及自身发展目标所坚持的追求与信念。大学最初由一群高度异质化的个体构成,要凝结成一个享有共同知识、价值和道德的共同体,则需使集体意识得以复苏,因而,“仪式必须保证信仰不能从记忆中抹去”。这一集体意识复苏的过程,体现为群体周期性更新自身与共同体情感的积极互动关系。大学成员通过仪式的组合、凝聚,体验到共同的身份带来的荣誉感和组织感,从而产生维持群体团结性的集体意识,最终形成一个共享知识、信仰、道德准则的校园共同体。比如,升旗、党团宣誓、开学典礼、社团成立等仪式行为,使仪式参与者接受校园生活中的政治、伦理、道德关系,也使现实的校园权力结构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强化;学位评定、文娱竞赛、颁奖典礼等,则是权力选择和群体竞争的“合谋”,体现大学知识生产的标准化裁决与典范表彰,不仅可以积聚、提升个体情感能量,也增进了群体团结与群体道德感的回归。
信仰透过大学仪式进行展演,内化为大学成员的价值信条和行为准则。大学的信仰,实质是一所大学优秀文化传统所体现的核心价值观,它只有通过大学成员的一致行动才能使大学担负起应有的历史使命,实现其特有的价值。大学仪式是大学的一种制度生活,通过对大学精神与文化的历时性传承和共时性展演,使其固定、凝结为相应的价值与行为准则,为全体大学成员所共同遵循并付诸实践。例如,作为一所大学价值诉求的重要表达,校训在不同仪式空间内反复宣示,本身就是一种提升个体自律、促进大学成员凝结的重要方式,也是大学获得外在认同和支持的一种重要途径。 在形形色色的大学仪式中,大学成员结成一个临时的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成员的对话、情感表达方式被规定为一定的行为规则和程序,师生在其中被不断灌输、确认大学及个体的信仰与责任,使大学信仰逐步内化为群体和个体的价值、思想感情和态度等,从而维系了大学校园的结构与秩序,最终构成大学制度乃至社会制度的重要部分。由此,大学文化、大学精神、大学理念借助大学仪式具化为面向群体和个体的价值共识和制度规约———道德守则与行为规范,嵌入他们的日常生活。
大学仪式促使大学成员将信仰转化为德性生活。道德是信仰的自我体现,德性追求是大学教育的基本面向所在:“失去道德热情的教育实际上是没有方向的教育,不知何方是自己的目的地。” 大学仪式为其成员提供一种充满德性的生活方式,是以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