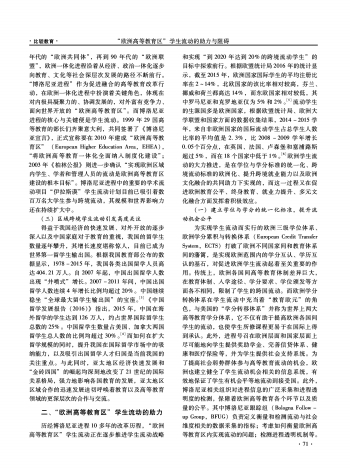年代的“欧洲共同体”,再到90年代的“欧洲联盟”,欧洲一体化进程沿着从经济、政治一体化逐步向教育、文化等社会深层次发展的路径不断前行。“博洛尼亚进程”作为促进融合的高等教育改革行动,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扮演着关键角色,体现在对内极具凝聚力的、协调发展的,对外富有竞争力、面向世界开放的“欧洲高等教育区”。而博洛尼亚进程的核心与关键便是学生流动。1999年29国高等教育的部长们齐聚意大利,共同签署了《博洛尼亚宣言》,正式宣称要在2010年建成“欧洲高等教育区”(EuropeanHigherEducationArea,EHEA),“将欧洲高等教育一体化全面纳入制度化建设”;2003年《柏林公报》则进一步确认“实现欧洲区域内学生、学者和管理人员的流动是欧洲高等教育区建设的根本目标”。博洛尼亚进程中的重要的学术流动项目“伊拉斯谟”学生流动计划目前已吸引着数百万名大学生参与跨境流动,其规模和世界影响力还在持续扩大中。
(三)区域跨境学生流动引发高度关注
得益于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对外开放的逐步深入以及中国家庭对于教育的重视,我国的留学生数量逐年攀升,其增长速度堪称惊人,目前已成为世界第一留学生输出国。根据我国教育部公布的数据显示,1978-2015年,我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高达404.21万人。自2007年起,中国出国留学人数出现“井喷式”增长。2007-2011年间,中国出国留学人数连续4年增长比例均超过20%。中国继续稳坐“全球最大留学生输出国”的宝座。 《中国留学发展报告(2016)》指出,2015年,中国在海外留学的学生达到126万人,约占世界国际留学生总数的25%。中国留学生数量占美国、加拿大两国留学生总人数的比例均超过30%。而如何在扩大留学规模的同时,提升我国在国际留学市场中的吸纳能力,以及吸引出国留学人才归国是当前我国的关注重点。与此同时,亚太地区经济快速发展和“金砖四国”的崛起均深刻地改变了21世纪的国际关系格局,强力地影响各国教育的发展,亚太地区区域合作的迅速发展迫切呼唤着教育以及高等教育领域的更深层次的合作与交流。
二、“欧洲高等教育区”学生流动的助力
历经博洛尼亚进程10多年的改革历程,“欧洲高等教育区”学生流动正在逐步推进学生流动战略和实现“到2020年达到20%的跨境流动学生”的目标中探索前行。根据欧盟统计局2016年的统计显示,截至2015年,欧洲国家国际学生的平均注册比率在2~14%,北欧国家的该比率相对较高,芬兰、挪威和荷兰都高达14%,而东欧国家相对较低,其中罗马尼亚和克罗地亚仅为5%和2%。流动学生的生源国多是欧洲国家,根据欧盟统计局、欧洲大学联盟和国家方面的数据收集结果,2014-2015学年,来自非欧洲国家的国际流动学生占总学生人数比率的平均值是2.3%,比2008-2009学年增长0.05个百分点,在英国、法国、卢森堡和塞浦路斯超过5%,而在18个国家中低于1%。欧洲学生流动的大力推进,是在学位与学分标准的统一化、跨境流动标准的欧洲化、提升跨境就业能力以及欧洲文化融合的共同助力下实现的,而这一过程又在促进欧洲教育公平、终身教育、就业力提升、多元文化融合方面发挥着积极效应。
(一)建立学位与学分的统一化标准,提升流动机会公平
为实现学生流动而实行的欧洲三级学位体系、欧洲学分累积与转换体系(EuropeanCreditTransferSystem,ECTS)打破了欧洲不同国家间和教育体系间的藩篱,是实现欧洲范围内的学分互认、学历互认的基石,对促进欧洲学生流动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传统上,欧洲各国间高等教育体制差异巨大,在教育体制、入学途径、学分要求、学位颁发等方面各不相同,限制了学生的跨国流动。而欧洲学分转换体系在学生流动中充当着“教育欧元”的角色,与美国的“学分转移体系”并称为世界上两大高等教育学分体系,它不仅有助于提高欧洲各国间学生的流动,也使学生所修课程更易于在国际上得到承认。此外,进程号召在欧洲层面和国家层面上尽可能地向学生提供奖助学金、完善信贷体系、健康和医疗保险等,并为学生提供社会支持系统。为了提高社会弱势群体参与高等教育流动的机会,欧洲也建立健全了学生流动机会相关的信息系统,有效地保证了学生有机会平等地流动到接受国。此外,博洛尼亚相关组织对进程信息的广泛采集和进程透明度的检测,保障着欧洲高等教育各个环节以及质量的公平。其中博洛尼亚跟踪组(BolognaFollow-upGroup,BFUG)负责定义衡量和检测流动与社会维度相关的数据采集的指标;考虑如何衡量欧洲高等教育区内实现流动的问题;检测进程透明机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