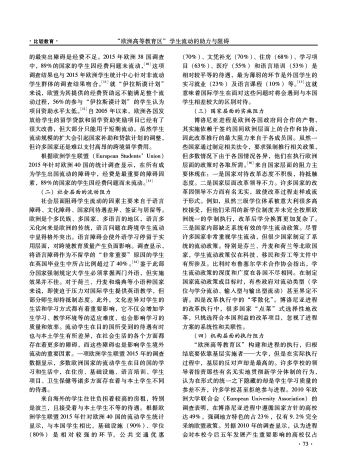的最突出障碍是经费不足。2015年欧洲38国调查中,89%的国家的学生因经费问题未流动, 这项调查结果也与2015年欧洲学生统计中心针对非流动学生群体的调查结果吻合。 就“伊拉斯谟计划”来说,欧盟为其提供的经费资助远不能满足整个流动过程,56%的参与“伊拉斯谟计划”的学生认为项目资助水平太低。 自2005年以来,欧洲各国发放给学生的留学贷款和留学资助奖励项目已经有了很大改善,但大部分只能用于短期流动。虽然学生流动规模的扩大会引起国家补助和贷款计划的调整,但许多国家还是难以支付高昂的跨境留学费用。
根据欧洲学生联盟(EuropeanStudents’Union)2015年针对欧洲40国的统计调查显示,在所有成为学生出国流动的障碍中,经费是最重要的障碍因素,89%的国家的学生因经费问题而未流动。
(二)社会层面的流动阻力
社会层面阻碍学生流动的因素主要来自于语言障碍、文化障碍、国家间待遇差异、签证与居留等。欧洲是个多民族、多国家、多语言的地区,语言多元化向来是欧洲的传统,语言问题在跨境学生流动中显得格外突出。语言障碍会使外语学习停留于实用层面,对跨境教育质量产生负面影响。调查显示,将语言障碍作为不留学的“非常重要”原因的学生在英国毕业生中所占比例超过了40%。 鉴于此部分国家强制规定大学生必须掌握两门外语,但实施效果并不佳。对于荷兰、丹麦和瑞典等小语种国家来说,即使迫于压力对国际学生提供英语教学,但部分师生却持抵制态度。此外,文化差异对学生的生活和学习方式都有着重要影响,它不仅会增加学生学习、教学环境等的适应难度,也会影响学习的质量和效率。流动学生在目的国所受到的待遇有时也与本土学生有所差异,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存在着更多的障碍,而这些障碍也是影响学生境外流动的重要因素。一项欧洲学生联盟2015年的调查数据显示,多数欧洲国家的流动学生在目的国的学习和生活中,在住房、基础设施、语言培训、学生项目、卫生保健等诸多方面存在着与本土学生不同的待遇。
来自海外的学生往往负担着较高的房租,特别是波兰,且接受着与本土学生不等的待遇。根据欧洲学生联盟2015年针对欧洲40国的流动学生统计显示,与本国学生相比,基础设施(90%)、学位(80%)是相对较强的环节,公共交通优惠(70%)、文凭补充(70%)、住房(68%)、学习项目(63%)、医疗(55%)和语言培训(53%)是相对较平等的待遇,最为薄弱的环节是外国学生的实习就业(23%)及语言课程(10%)等。 这就意味着国际学生在面对这些问题时将会遇到与本国学生相差较大的区别对待。
(三)国家层面的实施阻力
博洛尼亚进程是欧洲各国政府间合作的产物,其实施依赖于签约国间欧洲层面上的合作和协商,因此改革推行的最大阻力来自于各成员国。虽然一些国家通过制定相关法令,要求强制推行相关政策,但多数情况下由于各国情况各异,他们在执行欧洲层面的政策时各取所需。 来自国家层面的阻力主要体现在:一是国家对待改革态度不积极,持抵触态度。二是国家层面改革领导不力。许多国家的改革因领导不力而有名无实,致使改革过程走样或流于形式。例如,虽然三级学位体系被意大利很多高校接受,但他们采用的新学位制度并未完全按照欧洲统一的学制执行,改革后学分换算更加复杂了。三是国家内部缺乏系统有效的学生流动政策。尽管许多国家非常重视学生流动,但很少国家制定了系统的流动政策。特别是芬兰、丹麦和荷兰等北欧国家,学生流动政策仅在科技、移民和劳工等文件中有所涉及。比利时布鲁塞尔学术合作协会指出,学生流动政策的深度和广度在各国不尽相同。在制定国家流动政策或目标时,有些政府对流动类型(学位与学分流动、输入型与输出型流动)甚至界定不清。四是改革执行中的“零散化”。博洛尼亚进程的改革执行中,很多国家“点菜”式选择性地改革,只挑选符合本国利益的改革项目,忽视了进程方案的系统性和关联性。
(四)机构层面的执行阻力
“欧洲高等教育区”构建和进程的执行,归根结底要依靠基层实施者———大学,但是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基层的反对声却是最高的。许多学校的领导者指责那些有名无实地贯彻新学分体制的行为,认为在形式的统一之下隐藏的却是学生学习质量的参差不齐,许多学校甚至拒绝参与进程。2010年欧洲大学联合会(EuropeanUniversityAssociation)的调查表明,在博洛尼亚进程中遵循国家方针的高校达49%,强调地方特色的占23%,仅有9.2%完全采纳欧盟政策。另据2010年的调查显示,认为进程会对本校今后五年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高校仅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