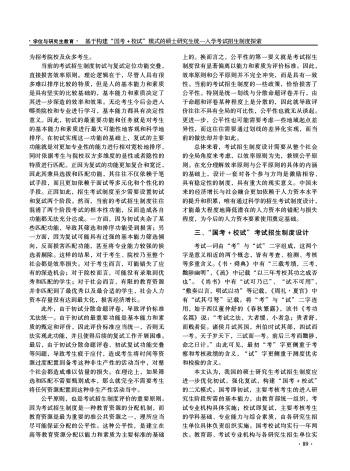为招考院校及众多考生。
当前的考试招生制度初试与复试定位功能交叠,直接损害效率原则。理论逻辑在于,尽管人具有很多难以排序比较的特质,但是人的基本能力和素质是具有坚实的比较基础的,基本能力和素质决定了其进一步深造的效率和效果。无论考生今后会进入哪类院校和专业进行学习,基本能力都具有决定性意义。因此,初试的最重要功能和任务就是对考生的基本能力和素质进行最大可能性地客观和科学地排序。在初试实现这一功能的基础上,复试的主要功能就是对更加专业性的能力进行相对宽松地排序,同时依据考生与院校双方多维度的显性或者隐性的特质进行匹配。正因为复试的功能更加复合和宽泛,因此其兼具选拔和匹配功能,其往往不仅依赖于笔试手段,而且更加依赖于面试等多元化和个性化的手段。正因如此,招生考试制度至少需要设置初试和复试两个阶段。然而,当前的考试招生制度往往混淆了两个阶段考试的根本性功能,反而造成各自功能都无法充分达成。一方面,因为初试夹杂了某些匹配功能,导致其筛选和排序功能受到损害;另一方面,因为复试可能具有过强的基本能力筛选倾向,反而损害匹配功能,甚至将专业能力较强的候选者剔除。这样的结果,对于考生、院校乃至整个社会都是效率损失。对于考生而言,可能错失了应有的深造机会;对于院校而言,可能没有录取到优秀和匹配的学生;对于社会而言,有限的教育资源并非匹配到了最优秀以及最合适的学生,社会人力资本存量没有达到最大化,损害经济增长。
此外,由于初试分散命题评卷,导致评价标准无法统一。由于初试的最重要功能是基本能力和素质的甄定和评价,因此评价标准应当统一,否则无法实现此功能,并且使得后续的复试工作开展困难。最后,由于初试分散命题评卷、初试复试功能交叠等问题,导致考生疲于应付,造成考生将时间等资源过度配置到备考这种非生产性的活动当中,对整个社会都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在理论上,如果筛选和匹配不需要甄别成本,那么就完全不需要考生将任何资源配置到这种非生产性活动当中。
公平原则,也是考试招生制度评价的重要原则。因为考试招生制度是一种教育资源的分配机制,而教育资源是最为重要的准公共资源之一,理所应当尽可能保证分配的公平性。这种公平性,是建立在高等教育资源分配以能力和素质为主要标准的基础上的。换而言之,公平性的第一要义就是考试招生制度没有显著偏离以能力和素质为评价标准。因此,效率原则和公平原则并不完全冲突,而是具有一致性。当前的考试招生制度的一些政策,恰恰损害了公平性。特别是统一划线与分散命题评卷并行,由于命题和评卷某种程度上是分散的,因此就导致评价往往不具有全局的可比性,公平性也就无从谈起。更进一步,公平性也可能需要考虑一些地域起点差异性,而这往往需要通过划线的差异化实现,而当前的做法却并非如此。
总体来看,考试招生制度设计需要从整个社会的全局角度来考虑,以效率原则为先,兼顾公平原则。在充分理解效率原则与公平原则的具体的内涵的基础上,设计一套对各个参与方均是激励相容、具有稳定性的制度,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与社会融合更加依赖于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和积累,唯有通过科学的招生考试制度设计,才能最大程度地降低潜在的人力资本的错配与损失程度,为今后的人力资本要素使用奠定基础。
三、“国考+校试”考试招生制度设计
考试一词由“考”与“试”二字组成,这两个字是意义相近的两个概念,皆有考查、检测、考核等多重含义。《书·舜典》中有“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疏》中记载“以三年考校其功之成否也”。《尚书》中有“试可乃已”、“试不可用”,“敷奏以言,明试以功”等记载,《周礼·夏官》中有“试其弓弩”记载。将“考”与“试”二字连用,始于西汉董仲舒的《春秋繁露》,该书《考功名篇》说:“考试之法,大者缓,小者急;贵者舒,而贱者促。诸侯月试其国,州伯时试其部,四试而一考。天子岁天下,三试而一考。前后三考而黜陟,命之曰计。”由此可见,最初“考”字更侧重于考察和考核政绩的含义,“试”字更侧重于测度优劣和检验的含义。
本文认为,我国的硕士研究生考试招生制度应进一步优化初试,强化复试,构建“国考+校试”的二元模式。国考即初试,主要考核考生的进入研究生阶段所需的基本能力,由教育部统一组织,考试专业机构具体实施;校试即复试,主要考核考生的学科基础、专业能力与综合素质,由各研究生招生单位具体负责组织实施。国考校试均实行一年两次。教育部、考试专业机构与各研究生招生单位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