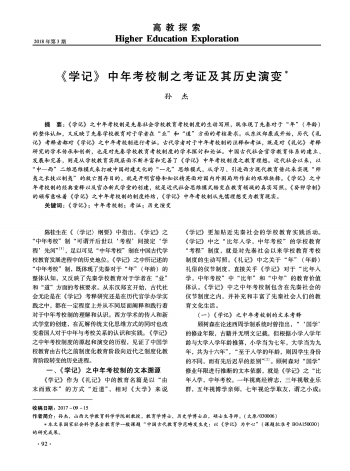孙 杰
摘 要:《学记》之中年考校制是先秦社会学校教育考校制度的生动写照,既体现了先秦对于“年”(年龄)的整体认知,又反映了先秦学校教育对于学者在“业”和“道”方面的考核要求。从东汉郑康成开始,历代《礼记》考释者都对《学记》之中年考校制进行考证。古代学者对于中年考校制的注释和考证,既是对《礼记》考释研究的学术传承和创新,也是对先秦学校教育考校制度的学术探讨和论证。中国古代社会官学教育体系的建立、发展和完善,则是从学校教育实践层面不断丰富和完善了《学记》中年考校制度之教育理想。近代社会以来,以“中—西”二维思维模式来打破中国封建文化的“一元”思维模式,从学习、引进西方现代教育借此来实现“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救亡图存目的,就是开明官僚和知识精英面对国内外困局所作出的艰难抉择。《学记》之中年考校制的经典重释以及官办新式学堂的创建,就是近代社会思维模式转变在教育领域的真实写照。《癸卯学制》的颁布意味着《学记》之中年考校制的制度终结,《学记》中年考校制从先儒理想变为教育现实。
关键词:《学记》;中年考校制;考证;历史演变
陈桂生在《〈学记〉纲要》中指出,《学记》之“中年考校”制“可谓开后世以‘考程’间接定‘学程’先河”,足以可见“中年考校”制在中国古代学校教育发展进程中的历史地位。《学记》之中所记述的“中年考校”制,既体现了先秦对于“年”(年龄)的整体认知,又反映了先秦学校教育对于学者在“业”和“道”方面的考核要求。从东汉郑玄开始,古代社会无论是在《学记》考释研究还是在历代官学办学实践之中,都在一定程度上并从不同层面阐释和践行着对于中年考校制的理解和认识。西方学术的传入和新式学堂的创建,在瓦解传统文化思维方式的同时也改变着国人对于中年与考校关系的认识和实践。《学记》之中年考校制度的源起和演变的历程,见证了中国学校教育由古代之前制度化教育阶段向近代之制度化教育阶段转变的历史进程。
一、《学记》之中年考校制的文本溯源
《学记》作为《礼记》中的教育名篇是以“由末而致本”的方式“近道”,相对《大学》来说《学记》更加贴近先秦社会的学校教育实践活动。《学记》中之“比年入学,中年考校”的学校教育“考程”制度,就是对先秦社会以来学校教育考校制度的生动写照。《礼记》中之关于“年”(年龄)礼俗的仪节制度,直接关乎《学记》对于“比年入学,中年考校”中“比年”和“中年”的教育价值体认。《学记》中之中年考校制包含在先秦社会的仪节制度之内,并补充和丰富了先秦社会人们的教育文化生活。
(一)《学记》之中年考校制的文本考释
顾树森在论述西周学制系统时曾指出,“‘国学’的修业年限,古籍并无明文记载,但根据小学入学年龄与大学入学年龄推算,小学当为七年,大学当为九年,共为十六年”,“至于入学的年龄,则因学生身份的不同,而有先后迟早的差别”。顾树森对“国学”修业年限进行推断的文本依据,就是《学记》之“比年入学,中年考校。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学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