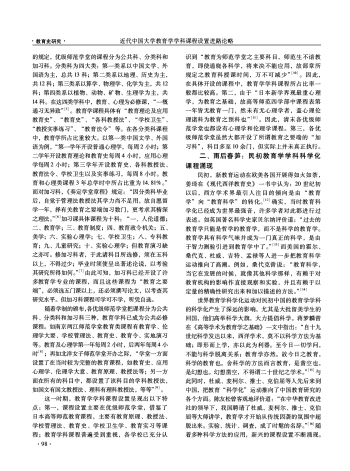随着学制的颁布,各优级师范学堂把课程分为公共科、分类科和加习科三种,教育学科已成为公共必修课程。如南京两江师范学堂教育类课程有教育学、伦理学大要、学校管理法、教育史、教育令、实地演习等。教育及心理学第一年每周2小时,后两年每周4小时[8];再如北洋女子师范学堂开办之际,“学堂一方面设置了在当时较为完整的教育课程,如教育史、应用心理学、伦理学大意、教育原理、教授法等;另一方面在所有的科目中,都设置了该科目的学科教授法,如国文有国文教授法、理科有理科教授法,等等”[9]。
这一时期,教育学学科课程设置呈现出以下特点:第一,课程设置主要在优级师范学堂,借鉴了日本高等师范教育课程,主要有教育原理、教授法、学校管理法、教育史、学校卫生学、教育实习等课程;教育学科课程普遍受到重视,各学校已充分认识到“教育为师范学堂之主要科目,师范生不谙教育,即使通晓各科学,将来决不能应用,故部章所规定之教育科授课时间,万不可减少”[10]。因此,在具体开设的课程中,教育学学科课程所占比率一般都比较高。第二,由于“日本新学界现最重心理学,为教育之基础,故高等师范四学部中课程表第一年皆无教育一门,然未有无心理学者,盖心理伦理诸科为教育之预科也”[11]。因此,清末各优级师范学堂也都设有心理学和伦理学课程。第三,各优级师范学堂虽然大都开设了所谓教育之要端的“加习科”,科目多至10余门,但实际上并未真正执行。
二、雨后春笋:民初教育学学科科学化课程涌现
民初,新教育运动在欧美各国开展得如火如荼,姜琦在《现代西洋教育史》一书中认为:20世纪初以后,西方学术界最引人注目的倾向是由“教育学”向“教育科学”的转化。[12]确实,当时教育科学化已经成为世界最强音,许多学者对此都进行过表述。如英国著名科学史家贝尔纳评价道:“过去的教育学只能是哲学的教育学,而不是科学的教育学。教育学具有科学气味并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是由于智力测验引进到教育学中了。”[13]而美国的霍尔、桑代克、杜威、吉特、孟禄等人进一步把教育科学运动推向了高潮。例如,桑代克曾说:“教育科学,当它在发展的时候,就像其他科学那样,有赖于对教育机构的影响作直接观察和实验,并且有赖于以定量的精确性研究出来和加以描述的方法。”[14]
世界教育学科学化运动对民初中国的教育学学科的科学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大批留美学生的回国,他们高举科学大旗,大力提倡科学。蒋梦麟曾在《高等学术为教育学之基础》一文中指出:“自十九世纪科学发达以来,西洋学术,莫不以科学方法为基础;即形而上学,亦以此为利器。至今日一切学问,不能与科学脱离关系;教育学亦然。故今日之教育,科学的教育也。舍科学的方法而言教育,是凿空也,是幻想也。幻想凿空,不得谓二十世纪之学术。”[15]与此同时,杜威、麦柯尔、推士、克伯屈等人先后来到中国,把教育“科学化”运动推向了中国教育研究的各个方面。陈友松曾客观地评价道:“在中华教育改进社的领导下,我国聘请了杜威、麦柯尔、推士、克伯屈等大师讲学,教育学才开始从传统因袭的氛围中超脱出来。实验、统计、调查,成了时髦的名辞。”[16]随着多种科学方法的应用,新兴的课程设置不断涌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