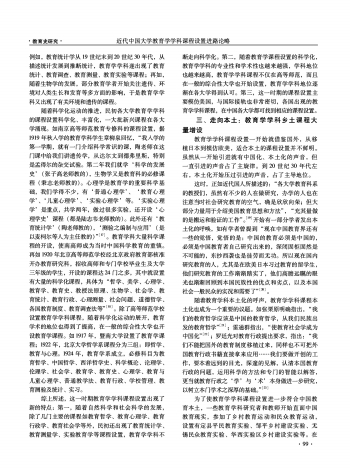随着科学化运动的推进,民初各大学教育学学科的课程设置科学化、丰富化,一大批新兴课程在各大学涌现。如南京高等师范教育专修科的课程设置,据1919年秋入学的教育学科学生章柳泉回忆,“我入学的第一学期,就有一门介绍科学常识的课,陶老师在这门课中给我们讲遗传学,从达尔文到德弗里斯,特别是孟得尔的杂交试验。第二年我们就学‘科学的发展史’(张子高老师教的),生物学又是教育科的必修课程(秉志老师教的)。心理学是教育学的重要科学基础,我们学得不少,有‘普通心理学’、‘教育心理学’、‘儿童心理学’、‘实验心理学’等。‘实验心理学’是重点,共学两年,做过很多实验,还开设‘心理学史’课程(都是陆志韦老师教的)。此外还有‘教育统计学’(陶老师教的),‘测验之编制与应用’(是以麦柯尔等人为主任教的)”[17]。教育学科大量科学课程的开设,使南高师成为当时中国科学教育的重镇。再如1920年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经北京政府教育部核准开办教育研究科,招收高师和专门学校毕业生及大学三年级的学生,开设的课程达24门之多,其中就设置有大量的科学化课程,具体为“哲学、美学、心理学、教育学、教育史、教授法原理、生物学、社会学、教育统计、教育行政、心理测量、社会问题、道德哲学、各国教育制度、教育调查法等”[18]。除了高等师范学校设置教育学学科课程,随着科学化运动的展开,教育学术的地位也得到了提高,在一般的综合性大学也开设教育学课程。如1917年,暨南大学设置了教育学课程;1922年,北京大学哲学系课程分为三组:即哲学、教育与心理。1924年,教育学系成立,必修科目为教育哲学、中国哲学、西洋哲学史、科学概论、论理学、伦理学、社会学、教育学、教育史、心理学、教育与儿童心理学、普通教学法、教育行政、学校管理、教育测验及统计、实习。
综上所述,这一时期教育学学科课程设置出现了新的特点:第一,随着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除了几门主要的课程如教育哲学、教育心理学、教育行政学、教育社会学等外,民初还出现了教育统计学、教育测量学、实验教育学等课程设置,教育学学科不断走向科学化。第二,随着教育学课程设置的科学化,教育学学科的专业性和学术性也越来越强,学科地位也越来越高,教育学学科课程不仅在高等师范,而且在一般的综合性大学也开始设置,教育学学科地位逐渐在各大学得到认可。第三,这一时期的课程设置主要模仿美国,与国际接轨也非常密切,各国出现的教育学学科课程,在中国各大学都可找到相应的课程设置。
三、走向本土:教育学学科乡土课程大量增设
教育学学科课程设置一开始就借鉴国外,从移植日本到模仿欧美,适合本土的课程设置并不鲜明。虽然从一开始引进就有中国化、本土化的声音,但一直引进的声音占了主旋律。到20世纪30年代左右,本土化开始压过引进的声音,占了主导地位。
这时,正如近代国人所描述的:“各大学教育科系的教授们,虽然有不少的人在做研究,办学的人也在注意当时社会研究教育的空气,确是欣欣向荣;但大部分力量用于介绍美国教育思想和方法”,“充其量做的是搬运和验证的工作”。[19]开始有一部分学者发出本土化的呼唤,如有学者曾提到“现在中国教育界还有一些的觉悟,觉悟的是:中国的教育必须是中国的,必须是中国教育者自己研究出来的,深闭固柜固然是不可能的,东抄西袭也是徒劳而无功。所以现在国内研究教育的人,尤其是在欧美日本习过教育的留学生,他们研究教育的工作渐渐踏实了,他们高瞻远瞩的眼光也渐渐回顾到本国民族性的优点和劣点,以及本国社会一般民众的实况和需要了”[20]。
随着教育学科本土化的呼声,教育学学科课程本土化也成为一个重要的议题。如张栗原明确指出,“我们的教育哲学应该是中国的教育哲学,从我们民族出发的教育哲学”[21];雷通群指出,“使教育社会学成为中国化”[22];罗廷光对教育行政提出要求,指出:“我们不能把国外的教育制度移植过来,同样也不可把外国教育行政书籍直接拿来应用……我们要做开创的工作,要本着远到的目光,深邃的见解,认清本国教育行政的问题,运用科学的方法和专门的智能以解答,更当就教育行政之‘学’与‘术’本身做进一步研究,以树立本门学术之深厚的基础。”[23]
为了使教育学学科课程设置进一步符合中国教育本土,一些教育学科研究者和教师开始直面中国教育现实,参加了乡村教育运动和民众教育运动,设置有定县平民教育实验、邹平乡村建设实验、无锡民众教育实验、华西实验区乡村建设实验等。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