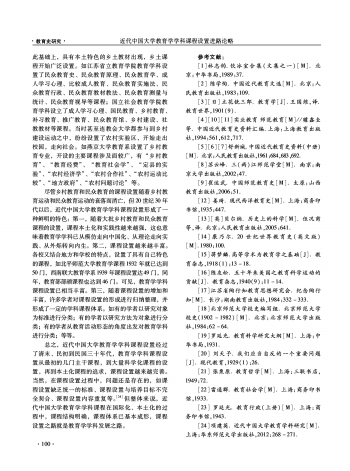尽管乡村教育和民众教育的课程设置随着乡村教育运动和民众教育运动的衰落而消亡,但20世纪30年代以后,近代中国大学教育学学科课程设置形成了一种鲜明的特色:第一,随着大批乡村教育和民众教育课程的设置,课程本土化和实践性越来越强,这也意味着教育学学科已从模仿走向中国化、从理论走向实践、从外烁转向内生。第二,课程设置越来越丰富。各校又结合地方和学校的特点,设置了具有自己特色的课程,如北平师范大学教育学课程1932年就已达到50门,西南联大教育学系1939年课程设置达49门,同年,教育部部颁课程也达到46门。可见,教育学学科课程设置已相当丰富。第三,随着课程设置的增加和丰富,许多学者对课程设置的形成进行归纳整理,并形成了一定的学科课程体系。如有的学者以研究对象为标准进行分类;有的学者以研究方法为对象进行分类;有的学者从教育活动形态的角度出发对教育学科进行分类;等等。
总之,近代中国大学教育学学科课程设置经过了清末、民初到民国三十年代,教育学学科课程设置从最初的几门主干课程,到大量科学化课程的设置,再到本土化课程的追求,课程设置越来越完善。当然,在课程设置过程中,问题还是存在的,如课程设置缺乏统一的标准、课程设置与培养目标不完全契合、课程设置内容重复等。[24]但整体来说,近代中国大学教育学学科课程在国际化、本土化的过程中,课程结构明确,课程体系已基本成形,课程设置之路就是教育学学科发展之路。
参考文献:
[1]林志钧.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M].北京:中华书局,1989:37.
[2]陈学恂.中国近代教育文选[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109.
[3][日]立花铣三郎.教育学[J].王国维,译.教育世界,1901(9).
[4][10][11]实业教育师范教育[M]//璩鑫圭等.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4:561,612,717.
[5][6][7]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中册)[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684,683,692.
[8]苏云峰.三(两)江师范学堂[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47.
[9]崔运武.中国师范教育史[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6:51.
[12]姜琦.现代西洋教育史[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447.
[13][英]贝尔纳.历史上的科学[M].伍况甫等,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641.
[14]康乃尔.20世纪世界教育史(英文版)[M].1980:100.
[15]蒋梦麟.高等学术为教育学之基础[J].教育杂志,1918(1):13-18.
[16]陈友松.五十年来美国之教育科学运动的贡献[J].教育杂志,1940(9):11-14.
[17]江苏省陶行知教育思想研究会.纪念陶行知[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332-333.
[18]北京师范大学校史编写组.北京师范大学校史(1902-1982)[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62-64.
[19]罗廷光.教育科学研究大纲[M].上海:中华书局,1931.
[20]刘天予.我们应当自反的一个重要问题[J].现代教育,1929(1):26.
[21]张栗原.教育哲学[M].上海:三联书店,1949:72.
[22]雷通群.教育社会学[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
[23]罗廷光.教育行政(上册)[M].上海:商务印书馆,1943.
[24]项建英.近代中国大学教育学科研究[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268-2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