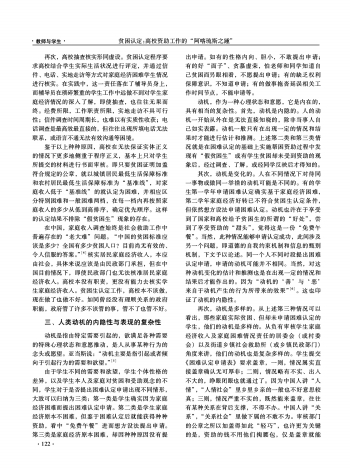鉴于以上种种原因,高校在无法保证实体正义的情况下更多地侧重于程序正义,基本上只对学生所提交的材料进行书面审核。即只要贫困证明加盖符合规定的公章,就以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和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为“基准线”,对家庭收入低于“基准线”的就认定为困难,并相应区分特别困难和一般困难两档,在每一档内再按照家庭收入的多少从低到高排序,确定优先顺序。这样的认定结果不排除“假贫困生”现象的存在。
在中国,家庭收入调查始终是社会救助工作中普遍存在的“老大难”问题。“中国的贫困标准应该是多少?全国有多少贫困人口?目前尚无有效的、令人信服的答案。”[4]核实居民家庭经济收入,本应由社会,具体来说应该是由民政部门承担,但在中国目前情况下,即使民政部门也无法核准居民家庭经济收入。高校本没有职责,更没有能力去核实学生家庭经济收入。贫困生认定工作,高校本不该做,现在做了也做不好。如同曾经没有理顺关系的政府职能,政府管了许多不该管的事,管不了也管不好。
三、人类动机的内隐性与表现的复杂性
动机是指由特定需要引起的,欲满足各种需要的特殊心理状态和意愿推动,是人从事某种行为的念头或愿望。亚当斯说:“动机主要是指引起或者倾向于引起行为的需要和欲望。”[5]
由于学生不同的需要和欲望,学生个体性格的差异,以及学生本人及家庭对贫困和受助观念的不同,学生对于是否提出困难认定申请出现不同情形,大致可以归纳为三类:第一类是学生确实因为家庭经济困难而提出困难认定申请。第二类是学生家庭经济原本不困难,但鉴于困难认定后就能获得种种资助,看中“免费午餐”进而想方设法提出申请。第三类是家庭经济原本困难,却因种种原因没有提出申请。如有的性格内向、胆小,不敢提出申请;有的好“面子”、贪慕虚荣,怕老师和同学知道自己贫困而另眼相看,不愿提出申请;有的缺乏权利保障意识,不知道申请;有的做事拖沓延误相关工作时间节点,不能申请等。
动机,作为一种心理状态和意愿,它是内在的,具有相当的复杂性。首先,动机是内隐的。人的动机一开始从外在是无法直接知晓的,除非当事人自己如实表露。动机一般只有在出现一定的情况和结果时才能进行估计和推测。上述第二类和第三类情况就是在困难认定的基础上实施帮困资助过程中发现有“假贫困生”或有学生贫困却未受到资助的现象后,经过调查、了解,或经同学反映后才得知的。
其次,动机是变化的。人在不同情况下对待同一事物或做同一举措的动机可能是不同的。有的学生第一学年申请困难认定确实基于家庭经济困难,第二学年家庭经济好转已不符合贫困生认定条件,但依然想方设法申请困难认定。动机也许在于享受到了国家和高校给予贫困生的所谓的“好处”,尝到了享受资助的“甜头”,觉得这是一份“免费午餐”。当然,此种情况能够申请认定成功,此间涉及另一个问题,即道德的自我约束机制和信息的甄别机制,下文予以论述。同一个人不同时段提出困难认定申请,申请的动机可能并不相同。当然,对这种动机变化的估计和推测也是在出现一定的情况和结果后才能作出的。因为“动机的‘善’与‘恶’来自于动机产生的行为所带来的效果”[6]。这也印证了动机的内隐性。
再次,动机是多样的。从上述第三种情况可以看出,那些家庭实际贫困、但却未申请困难认定的学生,他们的动机是多样的。从负有审核学生家庭经济收入及家庭困难情况责任的居委会(或村委会)以及街道乡镇社会救助所(或乡镇民政部门)角度来讲,他们的动机也是复杂多样的。学生提交《困难认定申请表》要求盖章,一则,情况属实直接盖章确认无可厚非;二则,情况略有不实、出入不大的,睁眼闭眼也就通过了。因为中国人讲“人情”,“人情社会”里乡里乡亲的一般也不好意思较真;三则,情况严重不实的,既然能来盖章,往往有某种关系在背后支撑,不得不办。中国人讲“关系”,“关系社会”里做下属的不敢不为。审核部门的公章之所以加盖得如此“轻巧”,也许更为关键的是,资助的钱不用他们掏腰包,仅是盖章就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