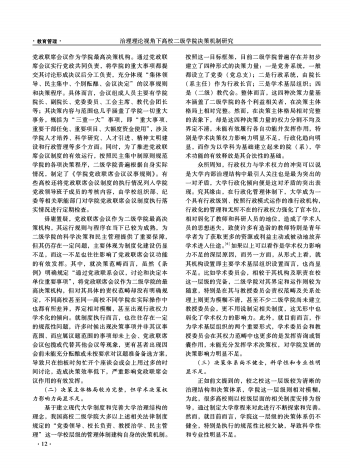毋庸置疑,党政联席会议作为二级学院最高决策机构,其运行规则与程序在当下已较为成熟,为二级学院的科学决策和民主管理提供了重要保障,但其仍存在一定问题,主要体现为制度化建设仍显不足,而这一不足也往往影响了党政联席会议功能的有效发挥。其中,就决策范畴而言,虽然《条例》明确规定“通过党政联系会议,讨论和决定本单位重要事项”,将党政联席会议作为二级学院的最高决策机构,但对其具体的责权范畴却没有明确规定,不同高校甚至同一高校不同学院在实际操作中也都有所差异,界定相对模糊,甚至出现行政权力学术化的倾向。就制度执行而言,也往往存在一定的规范性问题,许多时候出现决策事项并非其议事范围、而应属议题范围的事项却未上会、党政联席会议包揽或代替其他会议等现象,更有甚者出现因会前未能充分酝酿或未按要求对议题准备备选方案,导致只在拍板时匆忙开个座谈会或会上用过多的时间讨论,造成决策效率低下,严重影响党政联席会议作用的有效发挥。
(二)决策主体格局较为完整,但学术决策权力影响力尚显不足。
基于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和完善大学治理结构的理念,我国高校二级学院大多以上述相关法律制度规定的“党委领导、校长负责、教授治学、民主管理”这一学校层级的管理体制建构自身的决策机制。按照这一目标框架,目前二级学院普遍存在并初步建立了四种形式的决策力量:一是党务系统,一般都设立了党委(党总支);二是行政系统,由院长(系主任)作为行政长官;三是学术基层组织;四是(二级)教代会。整体而言,这四种决策力量基本涵盖了二级学院的各个利益相关者,在决策主体格局上相对完整。然而,在决策主体格局相对完整的表象下,却是这四种决策力量的权力分割不均及界定不清,未能有效履行各自功能并发挥作用,特别是学术决策权力影响力明显不足,行政化趋向明显,而作为以学科为基础建立起来的院(系),学术功能的有效释放是其合法性的基础。
众所周知,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冲突可以说是大学内部治理结构中最引人关注也是最为突出的一对矛盾,大学行政化倾向便是这对矛盾的突出表现。究其缘由,在行政化管理体制下,大学成为一个具有行政级别、按照行政模式运作的准行政机构,行政化的管理和无所不在的行政权力强化了官本位,相对弱化了教师和科研人员的地位,造成了学术人员的思想迷失,致使许多有造诣的教师特别是青年学者为了获取更多的资源或利益主动或被动地放弃学术进入仕途。[6]如果以上可以看作是学术权力影响力不足的深层原因,而另一方面,从形式上看,就其机构设置即主要学术基层组织设置而言,也尚显不足。比如学术委员会,相较于其机构及职责在校这一层级的完备,二级学院对其界定和运作则较为随意,特别是在其与教授委员会责权范畴及关系处理上则更为模糊不清,甚至不少二级学院尚未建立教授委员会,更不用说制定相关制度,这无形中也弱化了学术权力的影响力。此外,就目前而言,作为学术基层组织的两个重要形式,学术委员会和教授委员会在其权力范畴中也更多的是发挥咨询或智囊作用,未能充分发挥学术决策权,对学院发展的决策影响力明显不足。
(三)决策体系尚不健全,科学性和专业性明显不足。
正如前文提到的,较之校这一层级较为清晰的治理结构和决策体系,学院这一层级则相对模糊,为此,很多高校则以校级层面的相关制度安排为指导,通过制定大学章程来对此进行不断探索和完善。然而,就目前而言,学院这一层级的决策体系仍不健全,特别是执行的规范性比较欠缺,导致科学性和专业性明显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