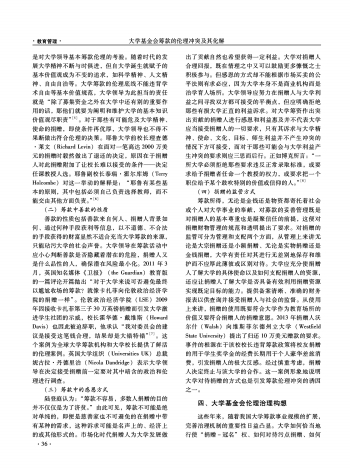(二)筹款中善款的性质
善款的性质包括善款来自何人、捐赠人背景如何、通过何种手段获利等信息,以不道德、不合法的手段获得的财富显然不适合充当大学筹款的来源,只能玷污大学的社会声誉。大学领导在筹款活动中应小心判断善款是否隐藏着潜在的危险,捐赠人又是什么品性的人,确保潜在风险最小化。2011年3月,英国知名媒体《卫报》(theGuardian)教育版的一篇评论开篇抛出“对于大学来说可否避免最终以尴尬收场的筹款?就像卡扎菲向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捐赠一样”。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2009年因接收卡扎菲第三子30万英镑捐赠而引发大学激进学生社团的示威,校长霍华德·戴维斯(HowardDavis)也因此被迫辞职,他承认“我对委员会的建议是接受这笔钱合理,结果却是大错特错”。[7]这个案例为全球大学筹款机构和大学校长提供了鲜活的伦理案例。英国大学组织(UniversitiesUK)总裁妮古拉·丹德里治(NicolaDandridge)表示大学领导在决定接受捐赠前一定要对其中暗含的政治和伦理进行调查。
(三)筹款中的感恩方式
陆登庭认为:“筹款不容易,多数人捐赠的目的并不仅仅是为了济贫。”由此可见,筹款不可能是绝对单纯的,即便是慈善家也不可避免的在捐赠中带有某种的需求,这种诉求可能是名声上的、经济上的或其他形式的。市场化时代捐赠人为大学发展做出了贡献自然也希望获得一定利益。大学对捐赠人合理回报,既在情理之中又可以鼓励更多慷慨之士积极参与。但感恩的方式却不能根据市场买卖的公平法则有求必应,因为大学本身不是商业机构而是治学育人场所。大学领导应努力在捐赠人与大学利益之间寻找双方都可接受的平衡点,但应明确拒绝那些有损大学正直的利益诉求。对大学筹资作出突出贡献的捐赠人进行感恩和利益惠及并不代表大学应当接受捐赠人的一切要求,只有其诉求与大学精神、使命、文化、目标、师生利益并不产生冲突的情况下方可接受,而对于那些可能会与大学利益产生冲突的要求则应三思而后行。正如博克所言:“一所大学必须拒绝那些要求违反正常录取标准,或要求给予捐赠者任命一个教授的权力,或要求把一个职位给予某个鼓吹特别的价值或信仰的人。”[8]
(四)捐赠的监管方式
筹款所得,无论是金钱还是物资都寄托着社会或个人对大学事业的奉献,对募款的妥善管理既是对捐赠人的基本尊重也是凝聚信任的前提,这便对捐赠财物管理的规范和透明提出了要求。对捐赠的监管可分为管理和支配两个方面,从管理上来讲无论是大宗捐赠还是小额捐赠、无论是实物捐赠还是金钱捐赠,大学有责任对其进行无差别地保存和维护而不应厚此薄彼或区别对待。大学应充分使捐赠人了解大学的具体使命以及如何支配捐赠人的资源,还应让捐赠人了解大学是否具备有效利用捐赠资源实现既定目标的能力。提供备案清晰、准确的财务报表以供查询并接受捐赠人与社会的监督。从使用上来讲,捐赠的使用既要符合大学作为教育场所的价值又要符合捐赠人的捐赠意愿。2013年捐赠人沃尔什(Walsh)向维斯菲尔德州立大学(WestfieldStateUniversity)提出了归还10万美元赠款的要求。事件的根源在于该校校长违背筹款政策将校友捐赠的用于学生奖学金的经费长期用于个人豪华差旅消费,引发捐赠人的极大反感。经过慎重考虑,捐赠人决定终止与该大学的合作。这一案例形象地说明大学对待捐赠的方式也是引发筹款伦理冲突的诱因之一。
四、大学基金会伦理治理构想
这些年来,随着我国大学筹款事业规模的扩展,完善治理机制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大学如何恰当地行使“捐赠-冠名”权、如何对待污点捐赠、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