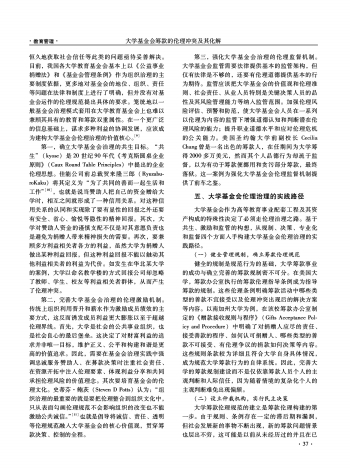第一,确立大学基金会治理的共生目标。“共生”(kyose)是20世纪90年代《考克斯圆桌企业原则》(CauxRoundTablePrinciples)中提出的企业伦理思想。佳能公司前总裁贺来隆三郎(RyuzaburoKaku)将其定义为“为了共同的善而一起生活和工作”[10],也就是说当赞助人把自己的资金赠给大学时,相互之间就形成了一种信用关系。对这种信用关系的认同和实现除了要有显性的回报之外还要有安全、省心、愉悦等隐性的精神回报。其次,大学对赞助人资金的谨慎支配不仅是对其意愿负责也是避免为捐赠人带来精神损失的需要。再次,要兼顾多方利益相关者各方的利益,虽然大学为捐赠人做出某种利益回报,但这种利益回报不能以触动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为代价。如发生在华北某大学的案例,大学以命名教学楼的方式回报公司却忽略了教师、学生、校友等利益相关者群体,从而产生了伦理冲突。
第二,完善大学基金会治理的伦理激励机制。传统上组织利用晋升和薪水作为激励成员绩效的主要方式,这反而诱发成员利益更大膨胀以至于超越伦理界线。首先,大学是社会的公共事业组织,也是社会良心的最后堡垒。这决定了对财富利益的追求并非唯一目标,维护正义、公平和构建和谐是更高的价值追求。因此,需要在基金会治理实践中强调忠诚服务赞助人、在募款决策时注重社会责任、在资源开拓中注入伦理要素、体现利益分享和共同承担伦理风险的价值理念。其次要培育基金会的伦理文化。史蒂芬·鲍茨(StevenDPotts)认为:“组织治理的最重要的就是要把伦理整合到组织文化中,只从表面勾画伦理规范不会影响组织的改变也不能激励公共诚信。”[11]也就是倡导将诚信、责任、透明等伦理规范融入大学基金会的核心价值观,贯穿筹款决策、控制的全程。
第三,强化大学基金会治理的伦理监督机制。大学基金会监管需要法律提供基本的监管架构,但仅有法律是不够的,还要有伦理道德提供基本的行为期待。监管应该把大学基金会的价值观和伦理准则、社会责任、从业人员特别是关键决策人员的品性及其风险管理能力等纳入监管范围。加强伦理风险评估、预警和防范,使大学基金会人员在一系列以伦理为内容的监管下增强道德认知和判断潜在伦理风险的能力;提升职业道德水平和应对伦理危机的公关能力。美国圣约翰大学前副校长CeciliaChang曾是一名出色的筹款人,在任期间为大学筹得2000多万美元,然而其个人品德行为却疏于监督,以为有功于筹款便挪用和贪污部分筹款,最终落狱。这一案例为强化大学基金会伦理监督机制提供了前车之鉴。
五、大学基金会伦理治理的实践路径
大学基金会作为高等教育事业配套工程及其资产构成的特殊性决定了必须走伦理治理之路。基于共生、激励和监管的构想,从规制、决策、专业化和监督四个方面入手构建大学基金会伦理治理的实践路径。
(一)健全管理规制,确立筹款伦理规范
健全的规制是规范行为的基础,大学筹款事业的成功与确立完善的筹款规制密不可分。在美国大学,筹款办公室执行的筹款伦理指导条例成为指导筹款的规制。这些伦理条例明确筹款活动中哪些类型的善款不宜接受以及伦理冲突出现后的解决方案等内容。以南加州大学为例,在该校筹款办公室制定的《赠款接收规则与程序》(GiftsAcceptancePolicyandProcedure)中明确了对捐赠人应尽的责任、接受善款的程序、如何认可捐赠人、哪些类型的善款不可接受、有伦理争议的捐款如何决策等内容。这些规则条款较为详细且符合大学自身具体情况,成为规范大学筹款行为的自律系统。因此,完善大学的筹款规制建设而不是仅依靠筹款人员个人的主观判断和人际信任,因为随着情境的复杂化个人的主观判断难免出现偏颇。
(二)设立仲裁机构,实行民主决策
大学筹款伦理规范的建立是筹款伦理构建的第一步。由于规则、条例存在一定的滞后期和漏洞,但社会发展新的事物不断出现,新的筹款问题情景也层出不穷,这可能是以前从未经历过的并且在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