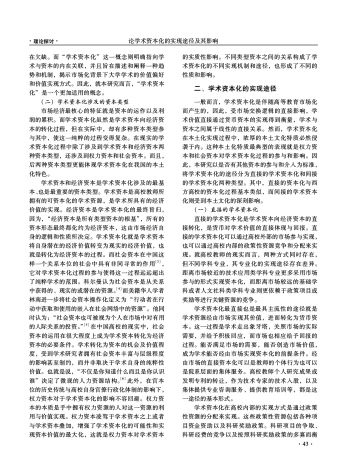(二)学术资本化涉及的资本类型
市场经济最核心的特征就是资本的运作以及利润的累积。而学术资本化虽然是学术资本向经济资本的转化过程,但在实际中,却有多种资本类型参与其中,使这一纯粹的过程变得复杂。在现实的学术资本化过程中除了涉及到学术资本和经济资本两种资本类型,还涉及到权力资本和社会资本。而且,后两种资本类型更能体现学术资本化在我国的本土化特色。
学术资本和经济资本是学术资本化涉及的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资本类型。学术资本是高校教师所拥有的可资本化的学术资源,是学术所具有的经济价值的实现。经济资本是学术资本化的最终旨归,因为,“经济资本是所有类型资本的根基”,所有的资本形态最终都化约为经济资本,这由市场经济自身的逻辑和性质所决定。学术资本化就是学术资本将自身潜在的经济价值转变为现实的经济价值,也就是转化为经济资本的过程。而社会资本在中国这样一个关系本位的社会中具有非同寻常的作用[3],它对学术资本化过程的参与使得这一过程远远超出了纯粹学术的范围。科尔曼认为社会资本是从关系中获得的、现实的或潜在的资源。[4]而美籍华人学者林南进一步将社会资本操作化定义为“行动者在行动中获取和使用的嵌入在社会网络中的资源”。他同时认为:“社会资本也可被视为个人在市场中对有用的人际关系的投资。”[5]在中国高校的现实中,社会资本的运用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学术资本转化为经济资本的必要条件。学术转化为资本的机会及价值程度,受到学术研究者拥有社会资本丰富与层级程度的影响甚至制约,而并非取决于学术自身的纯粹性价值。也就是说,“不仅是你知道什么而且是你认识谁”决定了微观的人力资源结构。[6]此外,在官本位的历史传统与高校自身官僚行政化体制的影响下,权力资本对于学术资本化的影响不容回避。权力资本的本质是手中握有权力资源的人对这一资源的利用与价值实现。权力资本凌驾于学术资本之上或者与学术资本叠加,增强了学术资本化的可能性和实现资本价值的最大化,这就是权力资本对学术资本的实质性影响。不同类型资本之间的关系构成了学术资本化的不同实现机制和途径,也形成了不同的性质和影响。
二、学术资本化的实现途径
一般而言,学术资本化是伴随高等教育市场化而产生的,因此,受市场交换逻辑的直接影响,学术价值直接通过货币资本的实现得到衡量,学术与资本之间属于线性的直接关系。然而,学术资本化在本土化实现过程中,浓厚的本土文化特质必然侵袭于内。这种本土化特质最典型的表现就是权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学术资本化过程的参与和影响。因此,本研究以是否有其他资本的参与和介入为标准,将学术资本化的途径分为直接的学术资本化和间接的学术资本化两种类型。其中,直接的资本化与西方高校的资本化过程基本类似,而间接的学术资本化则受到本土文化的深刻影响。
(一)直接的学术资本化
直接的学术资本化是学术资本向经济资本的直接转化,是货币对学术价值的直接体现与回报。直接的学术资本化可以通过高校外部的市场参与实现,也可以通过高校内部的政策性资源竞争和分配来实现。就高校教师的现实而言,两种方式同时存在,但不同学科专业,其专业化的实现途径存在差异。距离市场较近的技术应用类学科专业更多采用市场参与的形式实现资本化,而距离市场较远的基础学科或者人文社科类学科专业则更依赖于政策项目或奖励等进行关键资源的竞争。
学术资本化最直接也是最具主流性的途径就是学术资源经由市场实现其价值,进而转化为货币资本。这一过程是学术走出象牙塔,关照市场的实际需要,并给予积极回应,而市场也相应给予回报的过程。能否满足市场的需要,能否创造市场价值,成为学术能否经由市场实现资本化的前提条件。经由市场的直接资本化可以是教师的个体行为也可以是院系层面的集体服务。高校教师个人研究成果或发明专利的转让,作为技术专家的技术入股,以及集体提供专业咨询服务、提供教育培训等,都是这一途径的基本形式。
学术资本化在高校内部的实现方式是通过政策性资源的分配来实现。这些政策性资源包括各种项目资金资助以及科研奖励政策。科研项目的争取、科研经费的竞争以及按照科研奖励政策的多寡而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