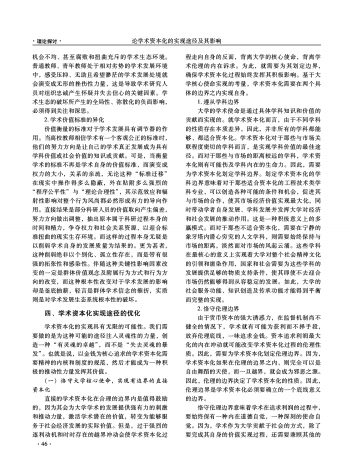2.学术价值标准的异化
价值衡量的标准对于学术发展具有调节器的作用。当高校教师相信学术有一个客观公正的标准时,他们的努力方向是让自己的学术真正发展成为具有学科价值或社会价值的知识或贡献。可是,当衡量学术的标准不再是学术自身的价值标准,而演变成权力的大小,关系的亲疏,无论这种“标准迁移”在现实中操作得多么隐蔽,外在贴附多么强烈的“程序公平性”与“理论合理性”,其示范效应和辐射性影响对整个行为风尚都必然形成有力的导向作用。直接结果是部分科研人员的价值取向产生偏差,努力方向做出调整,抽出原本属于科研过程本身的时间和精力,争夺权力和社会关系资源,以迎合标准扭曲的现实生存环境。而这样的过程本身无疑是以削弱学术自身的发展质量为结果的。更为甚者,这种削弱绝非以个别化、孤立性存在,而是带有很强的拓张性和感染性。伴随这种关键性影响因素改变的一定是群体价值观念及附属行为方式和行为方向的改变,而这种根本性改变对于学术发展的影响却是釜底抽薪,轻言是群体学术信念的摧折,实质则是对学术发展生态系统根本性的破坏。
四、学术资本化实现途径的优化
学术资本化的实现具有无限的可能性。我们需要做的是为这种可能的途径注入灵魂性的力量,创造一种“有灵魂的卓越”,而不是“失去灵魂的暴发”。也就是说,以金钱为核心追求的学术资本化需要精神的内核和制度的规范,然后才能成为一种积极的推动性力量发挥其价值。
(一)恪守大学核心使命,实现有边界的直接资本化
直接的学术资本化在合理的边界内是值得鼓励的,因为其会为大学学术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刺激和推动力量,激活学术潜在的价值,转变为能够服务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价值。但是,过于强烈的逐利动机和时时存在的越界冲动会使学术资本化过程走向自身的反面,背离大学的核心使命,背离学术伦理的内在诉求。为此,就需要为其划定边界,确保学术资本化过程始终发挥其积极影响。基于大学核心使命实现的考量,学术资本化需要在两个具体的边界之内实现自身。
1.遵从学科边界
大学的学术使命是通过具体学科知识和价值的贡献而实现的。就学术资本化而言,由于不同学科的性质存在本质差异,因此,并非所有的学科都能够、都适合资本化。学术资本化对于那些与市场关联程度密切的学科而言,是实现学科价值的最佳途径。而对于那些与市场的距离较远的学科,学术资本化则有可能伤及学科内在的生命力。因此,需要为学术资本化划定学科边界。划定学术资本化的学科边界意味着对于那些适合资本化的工程技术类学科专业,可以创造各种可能的条件和机会,促进其与市场的合作,使其市场经济价值实现最大化,同时带动学者自身发展、学科发展并发挥大学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这是一种积极意义上的多赢模式。而对于那些不适合资本化,需要在宁静的象牙塔内潜心穷究的人文学科,则需要始终保持与市场的距离,淡然面对市场的风起云涌。这些学科在最核心的意义上实现着大学对整个社会精神文化的引领和濡染作用,国家和社会需要为这些学科的发展提供足够的物质支持条件,使其即使不去迎合市场仍然能够得到从容稳定的发展。如此,大学的社会服务功能、知识创造及传承功能才能得到平衡而完整的实现。
2.恪守伦理边界
由于货币资本的强大诱惑力,在监督机制尚不健全的情况下,学术就有可能为获利而不择手段,放弃伦理底线,一味追求金钱。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内在冲动就可能改变学术资本化过程的伦理性质。因此,需要为学术资本化划定伦理边界。因为,学术资本化如果在伦理的边界之内,则完全可以是自由舞蹈的天使,而一旦越界,就会成为邪恶之源。因此,伦理的边界决定了学术资本化的性质。因此,伦理边界是学术资本化必须要确立的一个底线意义的边界。
恪守伦理边界意味着学术在追求利润的过程中,要始终保有一种内在道德自觉,一种深刻的使命自觉。因为,学术作为大学贡献于社会的方式,除了要完成其自身的价值实现过程,还需要兼顾其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