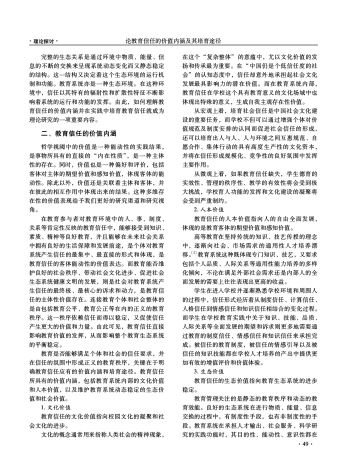二、教育信任的价值内涵
哲学视阈中的价值是一种能动性的实践结果,是事物所具有的直接的“内在性质”,是一种主体性的存在。同时,价值也是一种偏好和评价,包括客体对主体的期望价值和感知价值,体现客体的能动性。除此以外,价值还是关联着主体和客体,并在彼此的相互作用中体现出来的结果。这种多维存在性的价值表现给予我们更好的研究渠道和研究视角。
在教育参与者对教育环境中的人、事、制度、关系等肯定性反映的教育信任中,能够接受到知识、素质、精神等良好教育,并且能够在未来社会关系中拥有良好的生活保障和发展前途,是个体对教育系统产生信任的最集中、最直接的形式和体现,是教育信任的客体能动性的价值表达。而教育能否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带动社会文化进步、促进社会生态系统健康文明的发展,则是社会对教育系统产生信任的最终极、最核心的诉求和动力,是教育信任的主体性价值存在。连接教育个体和社会整体的是由包括教育公平、教育公正等在内的正义的教育秩序。这一秩序依赖信任而得以稳定,又促使信任产生更大的价值和力量。由此可见,教育信任直接影响教育价值的发挥,从而影响整个教育生态系统的平衡稳定。
教育是否能够满足个体和社会的信任要求,并在信任的氛围中形成正义的教育秩序,关键在于明确教育信任应有的价值内涵和培育途径。教育信任所具有的价值内涵,包括教育系统内部的文化价值和人本价值,以及维护教育系统动态稳定的生态价值和社会价值。
1.文化价值
教育信任的文化价值指向校园文化的凝聚和社会文化的进步。
文化的概念通常用来指称人类社会的精神现象,在这个“复杂整体”的意蕴中,尤以文化价值的发扬和传承最为重要。在“中国仍是个低信任度的社会”的认知态度中,信任却意外地承担起社会文化发展最具影响力的潜在价值。而在教育系统内部,教育信任在学校这个具有教育意义的文化场域中也体现出特殊的意义,生成自我主观存在性价值。
从宏观上看,培育社会信任是中国社会文化建设的重要任务,而学校不但可以通过增强个体对价值规范及制度安排的认同而促进社会信任的形成,还可以培育出人与人、人与环境之间互惠规范、自愿合作、集体行动的具有高度生产性的文化资本,并将在信任形成规模化、竞争性的良好氛围中发挥主要作用。
从微观上看,如果教育信任缺失,学生德育的实效性、管理的秩序性、教学的有效性将会受到极大挑战,学校育人功能的发挥和文化建设的凝聚将会受到严重制约。
2.人本价值
教育信任的人本价值指向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体现的是教育客体的期望价值和感知价值。
高等教育在坚持传统的知识、技艺传授的理念中,逐渐向社会、市场需求的通用性人才培养漂移。[2]教育系统这种既体现专门知识、技艺,又要求包括个人品质、人际关系等通用性能力培养的多样化倾向,不论在满足外部社会需求还是内部人的全面发展的需要上往往表现出更高的收益。
学生在进入学校并逐渐熟悉学校环境和周围人的过程中,信任形式经历着从制度信任、计算信任、人格信任到情感信任和知识信任相结合的变化过程。而学生在学校教育实践中关于知识、技能、品质、人际关系等全面发展的期望和诉求则更多地需要通过教育的制度信任、情感信任和知识信任来承担完成。被信任的教育制度,被信任的情感引导以及被信任的知识技能都在学校人才培养的产出中提供更加有效的增值评价和价值体验。
3.生态价值
教育信任的生态价值指向教育生态系统的进步稳定。
教育管理关注的是静态的教育秩序和动态的教育效能。良好的生态系统在进行物质、能量、信息交换的过程中,有制度性手段,也有非制度性的手段。教育系统在承担人才输出、社会服务、科学研究的实践功能时,其目的性、能动性、意识性都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