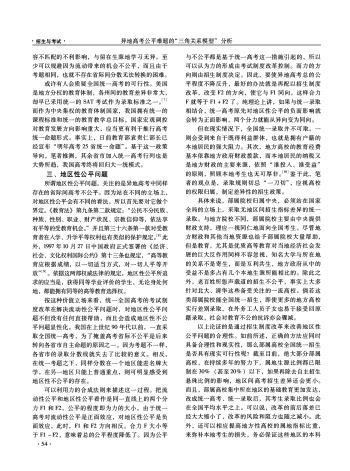或许有人会质疑全国统一高考的可行性。美国是地方分权的教育体制,各州间的教育差异非常大,却早已采用统一的SAT考试作为录取标准之一。[7]而作为中央集权的教育体制国家,我国拥有统一的课程标准和统一的教育教学总目标,国家宏观调控对教育发展方向影响重大,应当更有利于推行高考统一命题形式。事实上,日前教育部袁贵仁部长已经宣布“明年高考25省统一命题”。基于这一政策导向,笔者推测,其余省市加入统一高考行列也是大势所趋,我国高考终将回归大一统模式。
三、地区性公平问题
所谓地区性公平问题,关注的是异地高考中同样存在的省际间高考不公平。因为站在不同的立场上,对地区性公平会有不同的看法,所以首先要对它做个界定。《教育法》第九条第二款规定:“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财产状况、宗教信仰等,依法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并且第三十六条第一款对受教育者在入学、升学平等权利也有类似的保护规定。[8]此外,1997年10月27日中国政府正式签署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三条也规定,“高等教育应根据成绩,以一切适当方式,对一切人平等开放”[9]。依据这两部权威法律的规定,地区性公平所追求的应当是,获得同等学业评价的学生,无论身处何地,都能拥有同等的高等教育选择权。
按这种价值立场来看,统一全国高考的考试制度改革在解决流动性公平问题时,对地区性公平问题不但没有任何直接帮助,而且会造成地区性不公平问题显性化。我国在上世纪90年代以前,一直采取全国统一高考,为了掩盖高考省际不公平是后来转向各省市自主命题的原因之一。因为考题不一样,各省市的录取分数线就失去了比较的意义。相反,在统一考题之下,同样分数在一个地区能进名牌大学,在另一地区只能上普通重点,则可明显感受到地区性不公平的存在。
可以利用力的合成法则来描述这一过程。把流动性公平和地区性公平看作是同一直线上的两个分力F1和F2,公平的程度即为力的大小。由于统一高考对流动性公平是正面效应,对地区性公平是负面效应,此时,F1和F2方向相反。合力F大小等于F1-F2,意味着总的公平程度降低了。因为公平与不公平都是基于统一高考这一措施引起的,所以可以认为力的形成由考试制度改革控制。而力的方向则由招生制度决定。因此,要使异地高考总的公平程度不降反升,最好的办法就是再配以招生制度改革,改变F2的方向,使它与F1同向,这样合力F就等于F1+F2了。纯理论上讲,如果与统一录取相结合,统一高考原先对地区性公平的负面影响就会转为正面影响,两个分力就能从异向变为同向。
但在现实情况下,全国统一录取并不可取。一则会受到来自于既得利益群体,也就是拥有户籍的本地居民的强大阻力。其次,地方高校的教育经费基本依靠地方政府财政拨款,而本地居民的纳税又是地方财政的主要来源,依照“谁投入、谁受益”的原则,照顾本地考生也无可厚非。[10]鉴于此,笔者的观点是,录取规则切忌“一刀切”,应视高校的权限归属,制定差异性的招生政策。
具体来说,部属院校归属中央,必须站在国家全局的立场上,采取无地区间招生指标差异的统一录取。与地方院校不同,部属院校主要由中央提供财政支持,理应一视同仁地面向全国考生。尽管地方财政和其他当地资源也给予部属院校大量帮助,但是教育,尤其是优质高等教育对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反作用同样不容忽视,知名大学与所在地的关系不是寄生,而是互利共生,地方政府从中的受益不是多占有几个本地生源所能相比的。除此之外,老百姓所怨声载道的招生不公平,事实上大多针对北大、清华这些备受关注的一流高校。倘若这类部属院校能全国统一招生,即使更多的地方高校实行差别录取,在外务工人员子女也易于接受回原籍录取,社会对教育不公的抗诉亦会骤减。
以上论证的是通过招生制度改革来改善地区性公平问题的合理性。如前所述,正确的方法应同时具备合理性和现实性,那么部属高校全国统一招生是否具有现实可行性呢?截至目前,绝大部分部属高校,在持续多年的努力下,属地生源比例都已限制在30%(甚至20%)以下,如果再除去自主招生悬殊比例的影响,地区间高考招生差异还会更小。而且,部属高校集中所在地区的基础教育更加发达,改成统一高考、统一录取后,其考生录取比例也会在全国平均水平之上。可以说,改革的前后落差已经大大缩小了,改革的风险和阻力也随之减小。此外,还可以相应提高地方性高校的属地指标比重,来弥补本地考生的损失,务必保证这些地区的本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