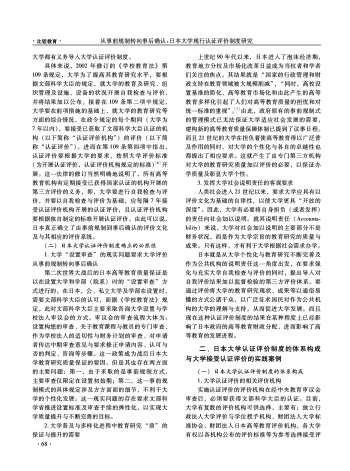具体来说,2002年修订的《学校教育法》第109条规定,大学为了提高其教育研究水平,要根据文部科学大臣的规定,就大学的教育及研究、组织管理及设施、设备的状况开展自我检查与评价,并将结果加以公布。接着在109条第二项中规定,大学要在前项措施的基础上,就大学的教育研究等方面的综合情况,在政令规定的每个期间(大学为7年以内),要接受已获取了文部科学大臣认证的机构(以下简称“认证评价机构”)的评价(以下简称“认证评价”)。进而在第109条第四项中指出,认证评价要根据大学的要求,按照大学评价标准(为开展认证评价,认证评价机构规定的标准)[6]开展。这一法律的修订当然明确地说明了,所有高等教育机构有定期接受已获得国家认证的机构开展的第三方评价的义务,即,大学要进行自我检查与评价,并要以自我检查与评价为基础,应每隔7年接受认证评价机构开展的认证评价,且认证评价机构要根据独自制定的标准开展认证评价。由此可以说,日本真正确立了由事前规制到事后确认的评价文化及与其相应的评价系统。
(二)日本大学认证评价制度确立的必然性
1.大学“设置审查”的现实问题要求大学评价从事前规制转向事后确认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高等教育质量保证是以在设置大学和学部(院系)时的“设置审查”方式进行的。在日本,公、私立大学及学部在设置时,需要文部科学大臣的认可,而据《学校教育法》规定,此时文部科学大臣主要采取咨询大学设置与学校法人审议会的方式。审议会的审查流程大体为:设置构想的审查、关于教育课程与教员的专门审查、作为学校法人的适切性与财务计划的审查、对申请者传达中期审查意见与要求修正申请内容、认可与否的判定、咨询等步骤。这一政策成为战后日本大学教育研究质量保证的要因。但是其也存在两方面的主要问题:第一,由于采取的是事前规制方式,主要审查仅限定在设置初始期;第二,这一事前规制模式的具体规定涉及方方面面的细节,不利于大学的个性化发展。这一现实问题的存在要求文部科学省推进设置标准及审查手续的弹性化,以实现大学质量提升与不断完善的目标。
2.大学普及与多样化进程中教育研究“质”的保证与提升的需要
上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进入了泡沫经济期,教育地方分权及市场化改革日益成为当权者和学者们关注的焦点。其结果就是“国家的行政管理和财政支持在教育领域被大规模削减”,“同时,高校设置基准的简化、高等教育市场化和由此产生的高等教育多样化引起了人们对高等教育质量的担忧和对统一标准的重视”。[7]由此,政府原有的事前规制式的管理模式已无法保证大学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建构新的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制已提到了议事日程。而且21世纪的大学在担负着使高等教育得以广泛普及作用的同时,对大学的个性化与各自的卓越性也都提出了相应要求。这就产生了由专门第三方机构对大学的教育研究质量加以评价的必要,以保证办学质量及彰显大学个性。
3.发挥大学社会说明责任的客观要求
人类社会进入21世纪以来,要求大学应具有以评价文化为基础的自律性,以使大学更具“开放的深度”。因此,大学有必要将自身担负(或者发挥)的责任向社会加以说明。就其说明责任(Accountability)来说,大学对社会加以说明的主要部分不是财务状况,而是作为大学宗旨的教育研究的质量与成果。只有这样,才有利于大学根据社会需求办学。
日本就是从大学个性化与教育研究不断完善及作为公共机构的说明责任这一角度出发,在要求强化与充实大学自我检查与评价的同时,提出导入对自我评价结果加以监督检验的第三方评价体系。要通过评价将大学的教育研究现状、成果等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公诸于众,以广泛征求国民对作为公共机构的大学的理解与支持,从而促进大学发展。而且现在这种认证评价制度的结果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影响了日本政府的高等教育财政分配,进而影响了高等教育的发展进程。
二、日本大学认证评价制度的体系构成与大学接受认证评价的实践案例
(一)日本大学认证评价制度的体系构成1.大学认证评价的相关评价机构
实施认证评价的评价机构在经中央教育审议会审查后,必须要获得文部科学大臣的认证。目前,大学有复数的评价机构可供选择,主要有:独立行政法人大学评价与学位授予机构、财团法人大学标准协会、财团法人日本高等教育评价机构,各大学有权以各机构公布的评价标准等为参考选择接受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