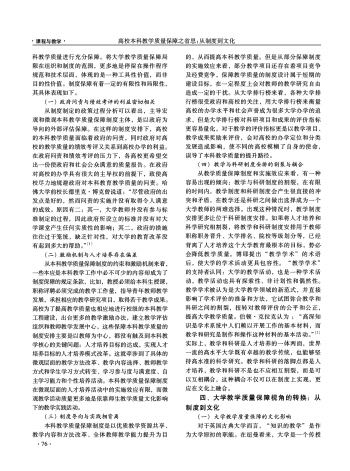(一)政府问责与绩效考评的利益密切相关
从制度制定的政策过程分析可以看出,主导宏观和微观本科教学质量保障制度主体,是以政府为导向的外部评估保障。在这样的制度安排下,高校的本科教学质量面临着政府的问责,同时政府对高校的教学质量的绩效考评又关系到高校办学的利益。在政府问责和绩效考评的压力下,各高校更希望交出一份使政府和社会公众满意的质量报告。在政府对高校的办学具有很大的主导权的前提下,致使高校尽力地规避政府对本科教育教学质量的问责。哈佛大学前校长德里克·博克曾说道:“尽管政府的出发点是好的,然而问责的实施并没有取得令人满意的成效。原因有二:其一,大学教师并没有参与标准制定的过程,因此政府所设立的标准并没有对大学课堂产生任何实质性的影响;其二,政府的措施往往过于笼统,缺乏针对性,对大学的教育改革没有起到多大的帮助。”[1]
(二)激励机制与人才培养存在偏差
从本科教学质量保障制度的约束和激励机制来看,一些本应是本科教学工作中必不可少的内容却成为了制度保障的规定条款,比如,教授必须给本科生授课,职称评聘必须完成的教学工作量,指导青年教师教学发展,承担相应的教学研究项目,取得若干教学成果。高校为了提高教学质量也相应地进行校级的本科教学工程建设,出台更多的教学激励办法,建立教学评估组织和教师教学发展中心,这些保障本科教学质量的制度安排主要是以教师为中心,都没有触及到本科教学核心的关键问题:人才培养目标的达成,实现人才培养目标的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这就牵涉到了具体的微观层面的教学方法改革、教学内容选择、教师教学方式和学生学习方式转变、学习参与度与满意度、自主学习能力和个性培养活动。本科教学质量保障制度在微观层面的人才培养活动中的实施效应有限,而微观教学活动质量更多地是依靠师生教学质量文化影响下的教学实践活动。
(三)制度导向与实践相背离
本科教学质量保障制度是以优质教学资源共享、教学内容和方法改革、全体教师教学能力提升为目的,从而提高本科教学质量。但是从部分保障制度的实施效应来看,部分教学项目还存在着项目竞争及经费竞争,保障教学质量的制度设计属于短期的建设目标,在一定程度上会对教师的教学研究自由造成一定的干扰。从大学排行榜来看,各种大学排行榜很受政府和高校的关注,用大学排行榜来衡量高校的办学水平和社会声誉成为很多大学办学的追求,但是大学排行榜对科研项目和成果的评价指标更容易量化,对于教学的评价指标更是以教学项目、教学成果奖励来评价,会对高校的办学定位和分类发展造成影响,使不同的高校模糊了自身的使命,误导了本科教学质量的提升路径。
(四)教学与科研制度安排的割裂与耦合
从教学质量保障制度和实施效应来看,有一种容易出现的倾向:教学与科研制度的割裂,在有限的时间内,教学制度和科研制度会产生很直接的冲突和矛盾,在教学还是科研之间做出选择成为一个大学教师的两难选择。出现这种情况时,教学制度安排更多让位于科研制度安排。如果将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相割裂,将教学和科研制度安排用于教师职称职务晋升、大学排名、院校等级划分等,已经背离了人才培养这个大学教育最根本的目标,势必会降低教学质量。博耶提出“教学学术”的术语后,使大学的学术活动更具包容性。“教学学术”的支持者认同:大学的教学活动,也是一种学术活动,教学活动也具有探索性、非计划性和偶然性。教学学术被认为是大学教学领域的新范式,并直接影响了学术评价的准备和方法,它试图弥合教学和科研之间的割裂,扭转对教师评价的公平和公正,提高大学教学质量。伯顿·克拉克认为:“高深知识是学术系统中人们赖以开展工作的基本材料,而教学和研究是制作和操作这种材料的基本活动。”[2]实际上,教学和科研是人才培养的一体两面,世界一流的高水平大学既有卓越的教学传统,也能够坚持高水准的科学研究。教学和科研的落脚点都是人才培养,教学和科研不是也不应相互割裂,而是可以互相耦合,这种耦合不仅可以在制度上实现,更应在文化上融合。
四、大学教学质量保障视角的转换:从制度到文化
(一)大学教学质量保障的文化影响
对于英国古典大学而言,“知识的教学”是作为大学原初的职能。在纽曼看来,大学是一个传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