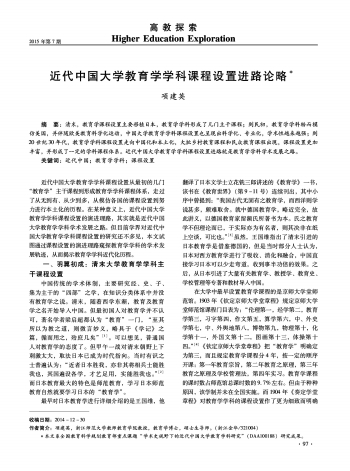摘 要:清末,教育学课程设置主要移植日本,教育学学科形成了几门主干课程;到民初,教育学学科转而模仿美国,并伴随欧美教育科学化运动,中国大学教育学学科课程设置也呈现出科学化、专业化,学术性越来越强;到20世纪30年代,教育学学科课程设置走向中国化和本土化,大批乡村教育课程和民众教育课程出现,课程设置更加丰富,并形成了一定的学科课程体系。近代中国大学教育学学科课程设置进路就是教育学学科学术发展之路。
关键词:近代中国;教育学学科;课程设置
近代中国大学教育学学科课程设置从最初的几门“教育学”主干课程到形成教育学学科课程体系,走过了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模仿各国的课程设置到努力进行本土化的历程。在某种意义上,近代中国大学教育学学科课程设置的演进理路,其实就是近代中国大学教育学学科学术发展之路。但目前学界对近代中国大学教育学学科课程设置的研究还不多见,本文试图通过课程设置的演进理路窥探教育学学科的学术发展轨迹,从而揭示教育学学科近代化历程。
一、羽翼初成:清末大学教育学学科主干课程设置
中国传统的学术体制,主要研究经、史、子、集为主干的“四部”之学,在知识分类体系中并没有教育学之说。清末,随着西学东渐,教育及教育学之名开始导入中国。但最初国人对教育学并不认可,著名学者梁启超都认为“教育”一门,“至其所以为教之道,则微言妙义,略具于《学记》之篇,循而用之,殆庶几矣”[1]。可以想见,普通国人对教育学的态度了。但甲午一战对清末朝野上下刺激太大,取法日本已成为时代指向。当时有识之士普遍认为:“近者日本胜我,亦非其将相兵士能胜我也,其国遍设各学,才艺足用,实能胜我也。”[2]而日本教育最大的特色是师范教育,学习日本师范教育自然就要学习日本的“教育学”。
最早对日本教育学进行详细介绍的是王国维,他翻译了日本文学士立花铣三郎讲述的《教育学》一书,该书在《教育世界》(第9-11号)连续刊出,其中小序中曾提到:“我国古代无固有之教育学,而西洋则学说甚多,颇难取舍。就中德国教育学,略近完全,故此讲义,以德国教育家留额氏所著书为本。氏之教育学不但理论而已,于实际亦为有名者,则其决非在纸上空谈,可比也。”[3]虽然,王国维指出了清末引进的日本教育学是借鉴德国的,但是当时部分人士认为,日本对西方教育学进行了吸收、消化和融合,中国直接学习日本可以少走弯道,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之后,从日本引进了大量有关教育学、教授学、教育史、学校管理等专著和教材导入中国。
在大学中最早设置教育学课程的是京师大学堂师范馆。1903年《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规定京师大学堂师范馆课程门目表为:“伦理第一,经学第二,教育学第三,习字第四,作文第五,算学第六,中、外史学第七,中、外舆地第八,博物第九,物理第十,化学第十一,外国文第十二,图画第十三,体操第十四。”[4]《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把“教育学”明确定为第三,而且规定教育学课程分4年,按一定的顺序开课:第一年教育宗旨,第二年教育之原理,第三年教育之原理及学校管理法,第四年实习。教育学课程的课时数占师范馆总课时数的9.7%左右。但由于种种原因,该学制并未在全国实施。而1904年《奏定学堂章程》对教育学学科的课程设置作了更为细致而明确
收稿日期:2014-12-30
作者简介:项建英,浙江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教授,教育学博士,硕士生导师。(浙江金华/321004)
本文系全国教育科学规划教育部重点课题“学术史视野下的近代中国大学教育学科研究”(DAA100188)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