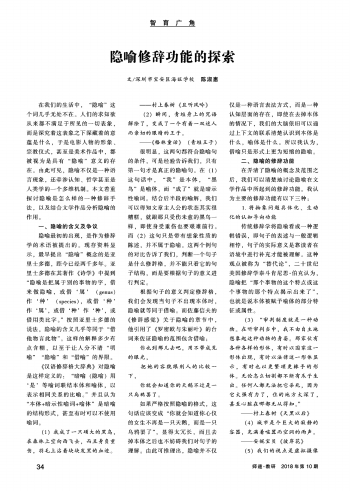在我们的生活中,“隐喻”这个词几乎无处不在。人们的求知欲从来都不满足于所见的一切表象,而是深究着这表象之下深藏着的意蕴是什么,于是电影人物的形象、宗教仪式,甚至是美术作品中,都被视为是具有“隐喻”意义的存在。由此可见,隐喻不仅是一种语言现象,还牵涉认知、哲学甚至是人类学的一个多维机制。本文着重探讨隐喻是怎么样的一种修辞手法,以及结合文学作品分析隐喻的作用。
一、隐喻的含义及争议
隐喻最初的出现,是作为修辞学的术语被提出的。现存资料显示,最早提出“隐喻”概念的是亚里士多德,距今已经两千多年。亚里士多德在其著作《诗学》中提到“隐喻是把属于别的事物的字,借来做隐喻,或借‘属’(genus)作‘种’(species),或借‘种’作‘属’,或借‘种’作‘种’,或借用类比字。”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隐喻的含义几乎等同于“借他物言此物”。这样的解释多少有点含糊,以至于让人分不清“明喻”“隐喻”和“借喻”的界限。
《汉语修辞格大辞典》对隐喻是这样定义的:“暗喻(隐喻)用‘是’等喻词联结本体和喻体,以表示相同关系的比喻。”并且认为“本体+暗示性喻词+喻体”是暗喻的结构形式,甚至有时可以不使用喻词。
(1)我成了一只硕大的黑鸟,在森林上空向西飞去,而且身负重伤,羽毛上沾着块块发黑的血迹。
——村上春树《且听风吟》
(2)瞬间,青蛙身上的咒语解除了,变成了一个有着一双迷人而亲切的眼睛的王子。
——《格林童话》(青蛙王子)
很明显,这两句都符合隐喻句的条件,可是经验告诉我们,只有第一句才是真正的隐喻句。在(1)这句话中,“我”是本体,“黑鸟”是喻体,而“成了”就是暗示性喻词。结合后半段的喻解,我们可以得知文章主人公的状态其实很糟糕,就跟那只受伤未愈的黑鸟一样,即使身受重伤也要艰难前行。而(2)这句只是带有想象性质的陈述,并不属于隐喻。这两个例句的对比告诉了我们,判断一个句子是什么修辞格,并不能只看它的句子结构,而是要根据句子的意义进行判定。
根据句子的意义判定修辞格,我们会发现当句子不出现本体时,隐喻就等同于借喻。而佐藤信夫的《修辞感觉》关于隐喻的章节中,他引用了《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台词来佐证隐喻的范围包含借喻:
你也到那儿去吧,用不带成见的眼光,
把她的容貌跟别人的比较一下,
你就会知道你的天鹅不过是一只乌鸦罢了。
如果严格按照隐喻的格式,这句话应该变成“你就会知道你心仪的女生不再是一只天鹅,而是一只乌鸦罢了”,显得太冗长,而且去掉本体之后也不妨碍我们对句子的理解。由此可推理出,隐喻并不仅仅是一种语言表法方式,而是一种认知层面的存在,即使在去掉本体的情况下,我们的大脑依旧可以通过上下文的联系清楚认识到本体是什么,喻体是什么。所以我认为,借喻只是形式上更为短缩的隐喻。
二、隐喻的修辞功能
在弄清了隐喻的概念及范围之后,我们可以清楚地讨论隐喻在文学作品中所起到的修辞功能。我认为主要的修辞功能有以下三种:
1. 将抽象问题具体化、生动化的认知导向功能
传统修辞学将隐喻看成一种逻辑错误,即句子的表述与一般逻辑相悖,句子的实际意义是靠读者在语境中进行补充才能被理解。这种观点被称为“替代论”,二十世纪美国修辞学泰斗肯尼思·伯克认为,隐喻把“那个事物的这个特点或这个事物的那个特点揭示出来了”,也就是说本体被赋予喻体的部分特征或属性。
(3)“审判制度就是一种动物。在听审判当中,我不由自主地想象起这种动物的身姿。那家伙有各种各样的形体,有时以国家这一形体出现,有时以法律这一形体显示,有时也以更繁琐更棘手的形体。无论怎么切割都不断有爪子生出。任何人都无法把它杀死,因为它太强有力了,住的地方太深了,甚至心脏在哪都无从得知。”
——村上春树《天黑以后》
(4)城市是个巨大的寂静的容器,充满着喧嚣而空洞的雨声。
——安妮宝贝《彼岸花》
(5)我们的视点是虚拟摄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