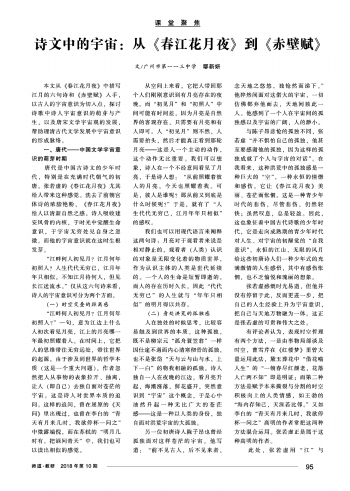本文从《春江花月夜》中描写江月的六句诗和《赤壁赋》入手,以古人的宇宙意识为切入点,探讨诗歌中诗人宇宙意识的萌芽与产生,以及唐宋文学宇宙观的发展,帮助理清古代文学发展中宇宙意识的形成脉络。
一、唐代——中国文学宇宙意识的萌芽时期
唐代是中国古诗文的少年时代,特别是在充满时代朝气的初唐,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尤其给人带来这种感觉。洗去了前朝宫体诗的浓脂艳粉,《春江花月夜》给人以清新自然之感。诗人吸收建安风骨的内核,于时光中觉醒生命意识,于宇宙无穷处见自身之忽微。而他的宇宙意识就在这时生根发芽。
“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仅从这六句诗来看,诗人的宇宙意识可分为两个方面。
(一)时空交叠的距离感
“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一句,意为江边上什么人初次看见月亮,江上的月亮哪一年最初照耀着人。在时间上,它把人的思维带往无穷远处,带往世界的起源。由于涉及到世界的哲学本质(这是一个重大问题),作者忽然把人从事物的表象拉开、抽离,让人(即自己)去独自面对苍茫的宇宙。这是诗人对世界本质的追问。这样的追问,曾在屈原的《天问》里出现过,也曾在李白的“青天有月来几时,我欲停杯一问之”中微露端倪,而在苏轼的“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中,我们也可以读出相似的感觉。
从空间上来看,它把人带回那个人们刚刚意识到有月亮存在的夜晚。而“初见月”和“初照人”中间可能有时间差,因为月亮是自然界的客观存在,只需要有月亮和有人即可。人“初见月”则不然,人需要抬头,然后才能真正看到那轮月亮——这是人一个主动的动作,这个动作无比重要。我们可以想象,诗人在一个不经意间看见了月亮,于是诗人想:“从前照耀着彼人的月亮,今天也照耀着我。可是,彼人是谁呢?那从前又到底是什么时候呢?”于是,就有了“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的感叹。
我们也可以用现代语言来阐释这两句诗:月亮对于观看者来说是相对静止的,观看者(人类)认识的对象是无限变化着的物质世界,作为认识主体的人类是世代延续的。一个人的生命是短暂即逝的,而人的存在历时久长。因此“代代无穷已”的人生就与“年年只相似”的明月得以共存。
(二)身处洪荒的孤独感
人在独处的时候思考,比较容易触及到世界的本质。这种孤独,既不是柳宗元“孤舟蓑笠翁”一样因仕途不遇而内心清寒彻骨的孤独,也不是张岱“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的物我相融的孤独。诗人独自一人在夜晚的江边,看月亮升起,海潮涨落,鲜花盛开,突然意识到“宇宙”这个概念,于是心中油然升起一种无比广大的苍茫感——这是一种以人类的身份,独自面对洪荒宇宙的大孤独。
另一位初唐诗人陈子昂也曾经孤独面对这样苍茫的宇宙。他写道:“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他猝然间面对这偌大的宇宙,一切仿佛都弃他而去,天地间独此一人。他感到了一个人在宇宙间的孤独感以及宇宙的广阔,人的渺小。
与陈子昂悲怆的孤独不同,张若虚“并不惧怕自己的孤独,他甚至要感谢他的孤独,因为这样的孤独成就了个人与宇宙的对话”。在我看来,这种洪荒中的孤独感是一种巨大的“空”,一种永恒的憧憬和感伤,它让《春江花月夜》美丽、苍茫而怅惘。这是一种青少年时代的悲伤,尽管悲伤,仍然轻快;虽然叹息,总是轻盈。因此,这也象征着中国古代诗歌的少年时代,它是走向成熟期的青少年时代对人生、对宇宙的初醒觉的“自我意识”。永恒的江山,无限的风月给这些初唐诗人们一种少年式的充满激情的人生感悟,其中有感伤怅惘,也不乏愉悦和瑰丽的想象。
张若虚感慨时光易逝,但他并没有停留于此,反而更进一步,把自己的人生经验上升为宇宙意识,把自己与天地万物融为一体。这正是张若虚的可贵和伟大之处。
有评论者认为,表现时空哲理有两个方法,一是由事物局部谈及时空,曹雪芹在《红楼梦》里曾大量运用此法,黛玉葬花中“借花喻人生”的“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即是明证;而第二种方法是赋予本来撕裂与分割的时空积极向上的人类情感,如王勃的“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又如李白的“青天有月来几时,我欲停杯一问之”高明的作者常把这两种方法混合运用。张若虚正是属于这种高明的作者。
此处,张若虚用“江”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