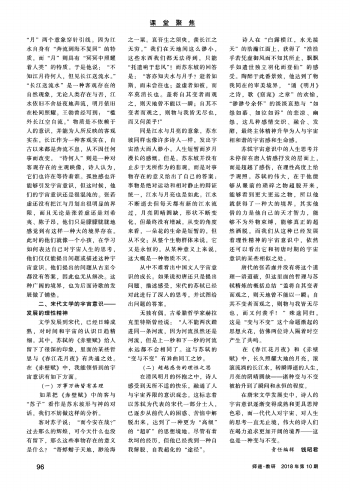二、宋代文学的宇宙意识——发展的理性精神
文学发展到宋代,已经日臻成熟,对时间和宇宙的认识日趋精细。其中,苏轼的《赤壁赋》给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里面的某些哲思与《春江花月夜》有共通之处。在《赤壁赋》中,我能领悟到的宇宙意识有如下方面。
(一)万事万物皆有其理
如果把《赤壁赋》中的客与“苏子”看作是苏东坡形与神的对话,我们不妨做这样的分析。
客对苏子说:“而今安在哉?”过去那么的辉煌,可今天什么也没有留下,那么这些事物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我们在天地间这么渺小,这些东西我们都无法得到,只能“托遗响于悲风”!而苏东坡的回答是:“客亦知夫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
同是江水与月亮的意象,苏东坡同样也像许多诗人一样,发出宇宙浩大而人渺小,人生短暂而岁月漫长的感慨。但是,苏东坡并没有止步于无所作为的悲观,而是对事物存在的意义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事物是绝对运动和相对静止的辩证统一,江水与月亮也是如此。江水不断逝去但每天都有新的江水流过,月亮阴晴圆缺,形状不断变化,但最终没有增减。从变的角度来看,一朵花的生命是短暂的,但从不变;从整个生物群体来说,它又是永恒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大概是一种物质不灭。
从中不难看出中国文人宇宙意识的成长。如果说初唐还只是提出问题、描述感受,宋代的苏轼已经对此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并试图给出问题的答案。
无独有偶,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里特斯曾经说:“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因为河流虽然还是河流,但是上一秒和下一秒的河流永远都不会相同了。这与苏轼的“变与不变”有异曲同工之妙。
(二)超越感伤的理性之思
在清风明月的怀抱之中,诗人感受到无所不适的快乐,融通了人与宇宙界限的意识观念。这标志着以苏轼为代表的宋代一部分士人,已逐步从前代人的困惑、苦恼中解脱出来,达到了一种更为“高级”的“超旷”的思想境地。尽管有着坎坷的经历,但他已经找到一种自我解脱、自我超化的“途径”。
诗人在“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的浩瀚江面上,获得了“浩浩乎若凭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的感受。陶醉于此番景致,他达到了物我同在的审美境界,“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的欢愉,“渺渺兮余怀”的淡淡哀愁与“如怨如慕、如泣如诉”的悲凉、幽怨,这几种感情交织、融合、发酵,最终主体精神升华为人与宇宙相和谐的宇宙感和生命感。
苏轼宇宙意识中的人生思考并未停留在唐人情感抒发的层面上,而是超越了感伤,在理性高度上给予观照。苏轼的伟大,在于他能够从眼前的琐碎之物超脱开来,能够看到更大更远之物,所以他就获得了一种大的境界。其实他借的力是他自己的天才智力,能够不为外物束缚,能够真正的超然洒脱。而我们从这种已经发展着理性精神的宇宙意识中,依然还可以看出它和初唐时期的宇宙意识的某些相似之处。
唐代的张若虚并没有将这个道理一语道破,但这里面的哲理与苏轼精炼的概括总结“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 ”殊途同归。这是“变与不变”这个命题激起的思想火花,仿佛两位诗人隔着时空产生了共鸣。
在《春江花月夜》和《赤壁赋》中,长久照耀大地的月亮,滚滚流淌的长江水,转瞬即逝的人生,月亮的阴晴圆缺——诸种变与不变被抬升到了瞬间和永恒的程度。
在唐宋文学发展史中,诗人的宇宙意识逐渐变得成熟和更具思辩色彩,而一代代人对宇宙、对人生的思考一直无止境,伟大的诗人们在竭力追求更加开阔的境界——这也是一种变与不变。
责任编辑 钱昭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