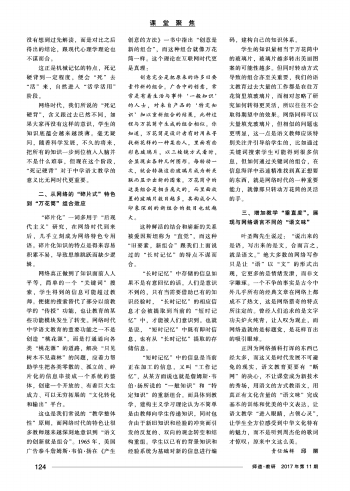这正是机械记忆的特点,死记硬背到一定程度,便会“死”去“活”来,自然进入“活学活用”阶段。
网络时代,我们所说的“死记硬背”,含义跟过去已然不同,如果大家再没有这样的意识,学生的知识底蕴会越来越淡薄。毫无疑问,随着科学发展,不久的将来,把所有的知识一步到位植入人脑并不是什么难事,但现在这个阶段,“死记硬背”对于中学语文教学的意义比无网时代更重要。
二、从网络的“碎片式”特色到“万花筒”组合效应
“碎片化”一词多用于“后现代主义”研究,在网络时代到来后,几乎立刻成为网络特色专用语。碎片化知识的特点是得来容易积累不易,导致思维跳跃而缺少逻辑。
网络真正做到了知识面前人人平等,简单的一个“关键词”搜索,学生得到的信息可能超过教师。便捷的搜索替代了部分以前教学的“传授”功能,也让教育的某些功能模块发生了转变。网络时代中学语文教育的重要功能之一不是创造“桃花源”,而是打通通向各类“桃花源”的道路,解决“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问题,应着力帮助学生把各类零散的、孤立的、碎片化的信息串接成一个系统的整体,创建一个开放的、有着巨大生成力、可以无穷拓展的“文化转化和输出”平台。
这也是我们常说的“教学整体性”原则,而网络时代的特色让很多教师越来越深刻地意识到“语文的创新就是组合”。1965年,美国广告泰斗詹姆斯·韦伯·扬在《产生创意的方法》一书中指出“创意是新的组合”,而这种组合就像万花筒一样。这个理论在互联网时代更是真理:
创意完全是把原来的许多旧要素作新的组合。广告中的创意,常常是有着生活与事件‘一般知识’的人士,对来自产品的‘特定知识’加以重新组合的结果,此种过程与万花筒中生成的组合相似。你知道,万花筒是设计者有时用来寻找新花样的一种某些人,里面有些彩色玻璃片,以三棱镜方式看时,会显现出各种几何图形。每转动一次,就会转换这些玻璃片成为新关联而显示出新的图案。万花筒中的这类组合是相当庞大的,而里面放置的玻璃片数目越多,其构成令人印象深刻的新组合的数目也就越大。
这种鲜活的结合和崭新的关系被爱因斯坦称为“直觉”,而这种“旧要素,新组合”跟我们上面说过的“长时记忆”的特点不谋而合。
“长时记忆”中存储的信息如果不是有意回忆的话,人们是意识不到的,只有当需要借助已有的知识经验时,“长时记忆”的相应信息才会被提取到当前的“短时记忆”中,才能被人们意识到。也就是说,“短时记忆”中既有即时信息,也有从“长时记忆”提取的存储信息。
“短时记忆”中的信息是当前正在加工的信息,又叫“工作记忆”,从某方面说也就是詹姆斯·韦伯·扬所说的“一般知识”和“特定知识”的重新组合。而具体到教学,建构主义学习理论认为不简单是由教师向学生传递知识,同时包含由于新旧知识和经验的冲突而引发的反复的、双向的观念转变和结构重组。学生以已有的背景知识和经验系统为基础对新的信息进行编码,建构自己的知识体系。
学生的知识量相当于万花筒中的玻璃片,玻璃片越多转出美丽图案的可能性越多。但同时转动方式导致的组合亦至关重要,我们的语文教育过去大量的工作都是在往万花筒里填玻璃片,而相对忽略了研究如何转得更灵活,所以往往不会取得期望中的效果。网络同样可以大量填充玻璃片,但相似的问题也更明显,这一点是语文教师应该特别关注并引导给学生的,比如通过关键词搜索学生可能得到很多信息,但如何通过关键词的组合,在信息海洋中迅速精准找到真正想要的东西,就是网络时代的一种重要能力,就像那只转动万花筒的灵活的手。
三、增加教学“垂直度”,展现与网络语言不同的“语文味”
叶圣陶先生说过:“说出来的是语,写出来的是文,合而言之,就是语文。”绝大多数的网络写作只是让“语”以“文”的形式出现,它更多的是情绪发泄,而非文字雕琢。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古今中外几乎所有的经典文章在网络上都成不了热文,这是网络猎奇的特点所注定的。曾经人们追求的是文字功夫炉火纯青,让人叹为观止,而网络造就的是标题党,是花样百出的吸引眼球。
正因为网络插科打诨的东西已经太多,而这又是时代发展不可避免的现实,语文教育更要有“断网”的决心,不让课堂成为新技术的秀场,用语文的方式教语文,用真正有文化含量的“语文味”完成基本的训练和优美的中文表达,让语文教学“进入眼睛,占领心灵”,让学生全方位感受到中华文化特有的魅力,而不是听到周杰伦的歌词才惊叹:原来中文这么美。
责任编辑 邱 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