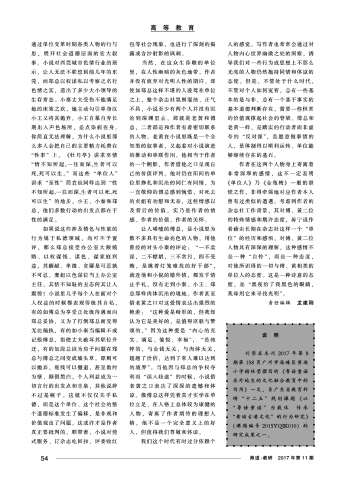如果说这些涉及情色与性欲的行为属于私德领域,尚可不予置评,那么郑总接受办公室大额贿赂、以权谋钱、谋色、谋家庭利益,其龌龊、卑微、贪鄙是可忍孰不可忍。糜姐以色谋位当上办公室主任,其恬不知耻的丑态何其让人震惊!小说里几乎每个人在面对个人权益的时候都表现得极其自私,有的如傅总为享受正处级待遇而向郑总妥协,又为了打倒郑总而变得无比偏执,有的如小秦当编辑不成记恨傅总,指使丈夫破坏其职位升迁,有的如段总因为房子问题在郑总与傅总之间变成墙头草。原则可以抛弃,底线可以撤退,甚至助纣为孽、颠倒黑白,个人利益成为一切言行的出发点和圭臬,其他说辞不过是幌子。这就不仅仅关乎私德,而是这个单位、这个社会的整个道德标准发生了偏移,是非观和价值观出了问题。这或许才是作者真正要批判的。顺带着,小说对莞式服务、订杂志吃回扣、评委收红包等社会现象,也进行了深刻的揭露或含沙射影的讽刺。
当然,在这众生昏聩的单位里,在人性幽暗的灰色地带,作者并没有放弃对光明人性的期许。即使如郑总这样不堪的人凌驾在单位之上,整个杂志社氛围混浊、正气不昌,小说至少有两个人并没有沉沦到深渊里去,那就是老黄和傅总,二者都是和作者有着密切联系的人物。老黄在小说里既是一个全知型的叙事者,又起着对小说演进的推动和串联作用。他相当于作者的一个侧影,作者借他之口呈现自己的价值评判。他对仍在阳间的单位里挣扎和沉沦的同仁有同情,为一直敬仰的傅总感到惋惜,对死去的贞姐有劝慰和无奈,这些情感以及背后的价值,实乃是作者的情感、作者的价值、作者的关怀。
让人唏嘘的傅总,是小说里为数不多具有生命亮色的人物,用他曾经的对头小秦的评论:“一不卖淫,二不嫖娼,三不贪污,四不受贿,是挑着灯笼难找的好干部”,就连他和小倪的婚外情,都发乎情止乎礼,没有走到小秦、小王、郑总那样肉体沉沦的境地。作者甚至借老黄之口对这爱情表达出强烈的艳羡:“这种爱是畸形的,但我却认为它是美好的,是值得讴歌与赞颂的,”因为这种爱是“内心的充实、满足、愉悦、幸福”,“是纯粹的,与金钱无关,与肉体无关,超越了世俗,达到了常人难以达到的境界”。当他因与郑总的争权夺利而“误入歧途”的时候,小说借老黄之口表达了深深的遗憾和体谅。像傅总这样凭着真才实学在单位立足、在人格上总体较为康健的人物,寄寓了作者期待的理想人格,他不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好人,但值得我们尊敬和体谅。
我们这个时代有时过分依赖个人的感觉,写作者也常常会通过对人物内心世界幽微之处的洞察,诱导我们对一些行为或思想上不那么光亮的人物仍然抱持同情和体谅的态度。但是,不管处于什么时代,不管对个人如何宽宥,总有一些基本的是与非,总有一个基于事实的基本道德判断存在,需要一些恒常的价值观撑起社会的脊梁。傅总和老黄一样,是踏实的行动者而非虚夸的“反对派”,是愿意做事情的人,是体制得以顺利运转、单位能够继续存在的基石。
作者在这两个人物身上寄寓着非常深厚的感情,这不一定表明《单位人》乃《金瓶梅》一般的泄愤之作,非得牵强地对应作者本人曾有过类似的遭遇。考虑到作者的杂志社工作背景,其对傅、黄二位的特殊情感和期许态度,毋宁说作者藉由长期在杂志社这样一个“单位”的经历和感悟,对傅、黄二位人物具有深深的理解,这种感情不是一种“自怜”,而是一种态度,对他所识得的一切与傅、黄相类的单位人的态度。这是一种诗意的态度,是“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
责任编辑 龙建刚
说 明
刊登在本刊2017年第8期第158页广州市海珠区黄埔小学谢林莹撰写的《粤语童谣在外地生的文化融合教育中的作用》一文,系广东省教育科研“十二五”规划课题《以“粤语童谣”为载体 传承“黄埔古港文化”的行为研究》(课题编号2015YQJK010)的研究成果之一。